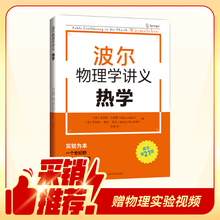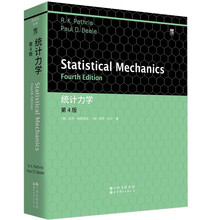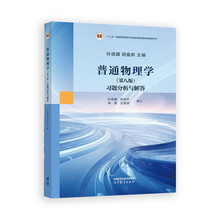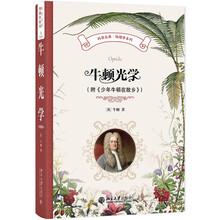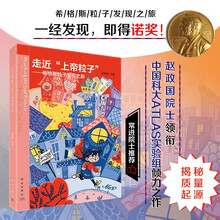第1章绪论
常规的流体力学研究是建立在局部平衡假设和连续介质假设之上的,相应的控制方程是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NS)方程,但适用前提是无量纲参数--克努森数(Knudsen数,简记为Kn,定义为分子平均自由程与流动特征
长度之比)较小。通常,根据该定义得到的Kn’可以将流动划分为连续流域(Kn<0.001)、滑移流域(0.00110少)。现代工业不断向更高、更快、更精方向发展,伴随出现的流体力学问题不再局限在小Kn范围内,比如稀薄气体环境下的流动和微纳尺度下的流动,这两个问题分别由于分子平均自由程很大以及流动特征长度很小而导致Kn很大,因此产生强烈的非平衡或非连续性效应。
对于非平衡和非连续性流动,传统的流体力学理论,如Navier-Stokes方程,以及基于此的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方法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不够准确,甚至可能完全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分子尺度的描述方法更为适用,这就引出了分子气体动力学的研究,其理论基础通常被称为分子动理论(kinetic theory)。分子动理论通过分析分子的速度分布、碰撞频率和动能等微观特性来推导出气体的宏观性质,如压力、温度和黏度等。玻尔兹曼(Boltzmann)方程则是在分子动理论框架下建立的一个重要方程,它描述了气体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在整个流域都是适用的,如图1.1所示。
1.1分子气体动力学的工程需求
分子气体动力学的发展与工程需求密切相关,已经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下面将从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超低轨卫星、微尺度气体流动、真空技术等方面进行介绍。
1.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
传统的航空飞行,飞行高度在20km以下,飞行器周围的流场都处于连续区。近几十年来,面向临近空间(地面以上20~100km)持续飞行的高超声速(马赫数(Ma)大于5)技术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各类新型高超声速飞行器不断涌现其具体形式主要包括滑翔再入高超声速飞行器丨如美国的HTV),高超声速吸气巡航飞行器(如美国的X-43A),低轨再入飞行器(如美国的X-37B),离地入轨飞行器(如英国的“云霄塔”),以及高超声速飞机等I凭借其特殊的飞行空域和较高的飞行速度,高超声速飞行器可以完成精确打击、情报收集等军事任务,以及快速运输、对地观测等民用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对高超声速气动特性的精确预测是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开发研制的基础保障与低速流动不同,高超声速流动包含了多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现象,如黏性干扰、稀薄气体效应、高温真实气体效应等。美国在2010年和2011年进行的两次HTV-2飞行试验均以失败告终,后续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主要的失败原因是对高超声速飞行的某些机理和规律认识不足,甚至还可能存在科学上的盲区。周恒院士和张涵信院士M在2015年发表的评述性文章中指出,“在空气稀薄处,高速空气动力学物理理论基础还不够坚实,存在新的空气动力学问题。"Hirschell8!在其专著中分析了不同类型高超声速飞行器面临的主要气动问题,指出稀薄气体效应和高温气体效应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大气密度降低,分子平均自由程(分子相邻两次碰撞间的平均距离)增大,稀薄气体效应变得愈发重要。具体而言,若选取飞行器机翼的特征长度为0.1m,根据美国1976年标准大气数据,在海平面,大气的密度约为1.225kg/m3,分子平均自由程约为60nm,此时Kn为6xl(T7,处于连续流域;当飞行高度增加到52km时,大气密度降低为7.67xl0_4kg/m3,分子平均自由程约为10_4m,Kn变成10_3,流动开始进入滑移区;当飞行高度增加到85km时,大气密度降低为6.77xl(T6kg/m3,分子平均自由程约为1(T2m,Kn变成0.1,流动开始进入过渡区;当飞行高度增加到112km时,大气密度降低为8.47xl0_7kg/m3,分子平均自由程约为1.0m,Kn变成10,流动为自由分子流,分子的个体行为占据主导地位。
在高超声速飞行中,由于任务需求多样化,飞行器可能通过多次变轨来改变飞行高度,从而可能跨越不同流域。在同一飞行高度,飞行器不同部位的周围流场也可能出现不同的非平衡状态。由于高升阻比和高机动性的要求,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一般采用尖头薄翼的外形设计,其前缘*率半径和翼尖厚度可小至毫米量级。因此,对于此类飞行器,即使某一飞行高度对应的全局Kn较小,在尖化前缘等局部区域也会存在稀薄气体效应,如图1.2所示。另一方面,高超声速飞行器需要克服严重的气动加热问题,为容纳不同结构间的热膨胀效应,飞行器表面留有许多小尺度的缝隙,这些缝隙处的局部流动同样可能存在稀薄气体效应。
前述提到的高温气体效应是高超声速飞行中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当飞行器以高超声速在大气层内飞行时,其前缘将会产生一道强激波。在激波和黏性摩擦的作用下,飞行器壁面周围空气温度急剧升高,形成严酷的气动加热环境。与此同时,空气的主要成分——氮气和氧气将出现振动激发、离解甚至电离等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此时,传统的“完全气体”假设不再成立,基于该假设的模型方程也会随之失效。气体的这种热化学性质的改变对流场及飞行器气动性能的影响一般被称为“高温真实气体效应”。高温真实气体效应与稀薄气体效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分子动理论的观点来看,分子的转动能和振动能激发、化学反应都是由分子之间的碰撞引起的。在稀薄情况下,分子碰撞频率降低,振动激发和化学反应的特征时间变长,更难以达到平衡状态。
稀薄气体效应和高温气体效应会严重影响气动力和气动热,给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气动预测带来困难。在气动力方面,孙泉华等总结了多种气动外形的临近空间飞行器在不同Kn下的升阻比数据,发现升阻比均随着稀薄程度的增加而明显下降。在气动热方面,王智慧的研究表明,由于稀薄气体效应和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尖化前缘的驻点温度相对于基于连续介质理论的Fay-Riddell公式给出的预测结果显著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高超声速情况下的非平衡效应不仅存在于气体流动过程,也存在于气体和固体壁面的相互作用过程,如图1.3所示。Candler在2019年指出,在高超声速条件下,有两类有限速率的气固相互作用过程对气动特性至关重要。**类是壁面滑移效应,包括速度滑移和温度跳跃,归属于稀薄效应。第二类是壁面催化效应,可归属于高温气体效应,具体而言,在高温流场中离解产生的氧原子和氮原子在热防护材料的催化作用下,可能会复合生成氧气和氮气分子,同时释放出结合能,对气动热产生显著影响。从分子动理论的观点来看,固体壁面的滑移效应和催化效应都是由气体分子或原子与固体壁面原子的相互作用过程引起的,如图1.3所示,因此滑移系数和催化反应速率分别与气体在壁面处的适应系数和催化复合系数直接相关。适应系数表征了从壁面反射的气体分子适应壁面宏观量的程度,而催化复合系数表征了与壁面碰撞的原子复合成分子的概率,两者的数值都在0到1之间。目前,气固相互作用模型尚未完善,通过实验方法测量得到的适应系数和催化复合系数也十分有限。
2.超低轨卫星
近年来,超低地球轨道(very low earth orbit,VLEO)卫星成为空间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超低地球轨道通常被定义为轨道高度在350km以下的空间环境。相比于传统卫星,超低轨卫星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例如提高对地观测分辨率、改善数据传输速率、减少有效载荷尺寸与质量、降低卫星开发和发射成本,以及减小碎片碰撞风险等。此外,超低轨卫星编队在导航增强、星群打击等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因此,各国已竞相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项目或计划。例如,欧洲空间局(ESA)于2009年发射了地球重力场和稳态海洋环流探测卫星(GOCE),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于2017年发射了用于研究超低轨环境中原子氧效应的超低空测试卫星(SLATS)等。在国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于2016年成功发射了稀薄大气科学实验卫星“力星一号”,是迄今为止以近圆轨道运行的高度*低的人造地球卫星。
然而,超低轨卫星也有其固有劣势。如图1.4所示,在超低轨环境下,大气分子与卫星表面之间碰撞所引起的大气阻力不可忽略,直接影响卫星运行的姿态、轨道和寿命,给卫星长期在轨运行带来了挑战。在超低轨环境下,大气阻力是卫星所受扰动的主要来源,这种扰动会对卫星的姿态控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超低轨卫星,特别是重力梯度测量卫星,实现精确测量的前提是消除大气阻力等非地球重力因素带来的扰动[16]。大气阻力也是确定和预测卫星轨道的关键影响因素。对气动阻力的准确预测可以提高卫星任务分析和轨道预测的准确性,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确定和跟踪卫星的轨道,从而避免卫星与空间碎片碰撞[1叱此外,大气阻力是决定超低轨卫星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在超低轨道环境下,一旦维持轨道的燃料耗尽,卫星将在大气阻力的作用下迅速脱轨,*终重返大气层并烧毁。因此,为了提高超低轨卫星气动阻力的预测精度,延长其在轨使用寿命,超低轨卫星气动阻力的计算分析与减阻设计成为目前需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
对于超低地球轨道环境,大气足够稀薄,气体流动属于自由分子流领域。一般认为,在大约130km的高度以上,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达10m,对于特征长度为lm的卫星,其飞行绕流均属于自由分子流[21L因此,超低轨卫星气动阻力的计算属于自由分子流空气动力学的范畴,具体可参见本书的第5章。
3.微尺度气体流动
微尺度气体流动广泛存在于微尺度器件中。早在1959年,Feynman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的演讲中就设想了利用芯片加工技术制造微小器件的可能性。随着微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微加工技术日益成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的概念。MEMS不仅具有运动、探测等功能,还嵌有用于控制的电子线路,两者相辅相成。MEMS的空间分辨率在微米量级,时间分辨率在微秒或更小量级。现有的MEMS装置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基于MEMS技术的安全“气囊”已在汽车中广泛采用,有效地降低了交通事故中的人员伤亡。
伴随MEMS出现的微流控系统,包括微流体的传感、输送、检测和控制,通常由微型泵、微型阀和微型传感器构成,可控制流体的压力、流量和流动方向。电子工业中的微流控芯片内部设置有各种微型通道和微型阀门,通过对通道内流体的精确控制,可实现芯片上试样的分离分析。微流控系统还可以应用到航天领域的微型发动机、电推进系统内的流动控制。例如,田立成等在其研制的LHT-100霍尔电推进系统中大量采用了微流量控制阀,以保证电推进系统对流量精确控制的需求。
微尺度气体流动应用的另一个实例是微型气体轴承。气体轴承以周围环境的气体为润滑介质,具有结构简单、免维护、可靠性高和适应性强等优点。目前,气体轴承已广泛应用于高转速精密工程、透平机械、空间技术、医疗器械设备和电子精密仪器等领域。随着微型飞行器的推进系统、燃料电池的空气补给管理系统、各类机器人的涡轮发电机等微型涡轮机械和微动力机电系统的发展,关于微型气体轴承的研究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对于宏观尺寸轴承来说,微型轴承的作用机理更为复杂,因为其尺寸较小,转速极高,需要从分子水平出发进行考虑分析。
近几十年来,作为*重要的数据载体的硬盘存储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磁头/磁盘形成的空气轴承界面是硬盘驱动器中*关键的部位,因为在该界面处直接发生读/写过程,而该过程是整个硬盘系统的主要功能。为了提高硬盘的存储密度,降低磁头与磁盘间的间隙是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方法。目前,磁头与磁盘之间的间隙已经达到了纳米级别,不到气体分子自由程的1/10,分子的个体行为变得愈发重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