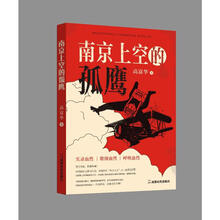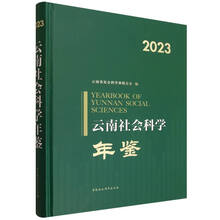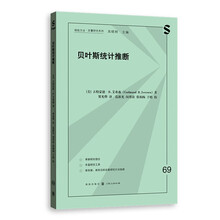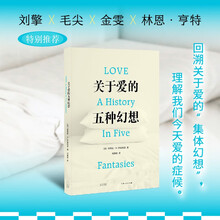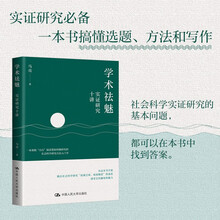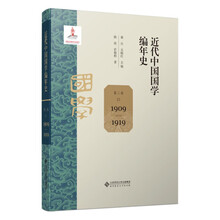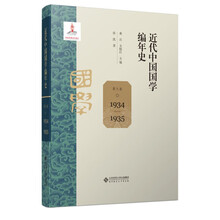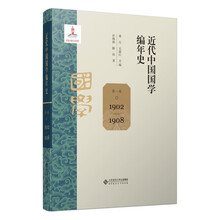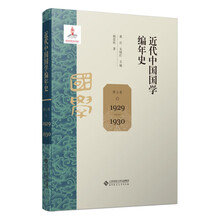《中国民族性研究与社会心理建设:沙莲香纪念文集》:
沙:第三本《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在思考上与以往不同,一个我写的是个体,再一个我写的是反思与批判。第三本书我放开来写,写我自己的想法和担忧。这本书对这些个案的解释,我留了很大的空间,不是按照通常人们的看法,甚至有时候是违背了一些舆论的看法。在解读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有反过来看的意识。
我来举例子。2003年“非典”时期大家关注的是恐惧和怎样应对的问题。我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学生群体里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当时已经被隔离在校园里,学生对政府的配合就是在校园隔离。“非典”过后,学生在课堂上讲述“非典”时,我才知道他们每天等到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活动时间——几乎倾巢而出,跳绳啊打球啊踢毽子啊,把所有小时候玩的全都玩过了,差一点就要在地上趴着玩了,欢快得不得了。这让我意识到,他们在隔离起来的天地里天真快乐的本性出来了。由于是当老师的,我格外注意的就是学生的真性情。他们希望自由自在,不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束缚,不要让他们戴着枷锁学习。而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给予学生太多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写“非典”,着重写大学生对自由的要求。有个女生在“非典”时给我写了封邮件,说她看到两个学生抱着球往操场跑时,一下子就没有了恐惧。大家都说“非典”来了,要关起大门。但是学生的天性、本能性的东西就是希望自由自在的,没有那么多的框框。我在《中国民族性(三)》里边谈到,为人老师,总是有一些反思。我们过去对学生的评价是越听话越是好学生,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是听话的学生得到。在我的学生里有不听话的,有被看作“刺头”的,但是在我的感觉里,越是这样的孩子,越有主见,这种孩子,他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他没有那种伪装的、伪善的东西。对于“非典”,大家看到的都是当时人们怎么紧张,却少有人看到人群里这些源于本性的真正的东西。再有就是对孙志刚事件的解释。我当时看到这个事件以后保留了网络上的各种文档。南方那个报纸对这个事情追踪得很具体,我当时很有感触。所幸的是,在滕彪等法律界人士的努力下,政府修改了收容条例。孙志刚的父亲在法庭上说他的儿子没有白死,使法律得到了修改。我注意到,舆论赞扬这位父亲“了不起”,儿子死了想到的是还给国家起到了一点作用。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我们的脑袋里面有“一根筋”,是过去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牺牲个人,顾全大局。这个观念在人们的脑袋里根深蒂固,碰到个人与社会之间某种纠葛问题时就容易给出这样的一种解释。在我看来这是不近人情的解释,是以损伤个人为代价的服从大局。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因此,我在书中说,孙志刚父亲的那句“悲痛”,表明孙家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也太无可奈何了。
对吴廷嘉的解释是又一个个案。她的死是悲惨的,而且是一种带有制度性的恶果,我很抱不平。她是个很有才、很有个性的学生。我之所以能认识她,是因为她当时是我校国政系的学生,“文革”前的本科生。我对她印象很深,当时在上课的时候就听她的同学说她非常有个性。有一次她跟男生打赌,说她要是输了可以剃光头,后来她输了,真的剃了光头。在她去世后,她的同事和挚友刘志琴教授写悼文《哀哉,吴廷嘉!》以悼念挚友。志琴洒泪而言:“她走了。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当医生宣布她患绝症,并多次做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后,她却又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她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这是我初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这个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她最后的安宁。”这是我从志琴长长的悼文中摘取的一小段。我书里采用的是戴逸老师在文集里写吴廷嘉的那段,那也是很感人的。戴老师说,她很有才又很爱管闲事,去帮这个,去帮那个,就是现在的志愿者精神,可是她是一身病痛,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儿子),实际上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要用现在的语言和眼光来看吴廷嘉,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知识分子。我写吴廷嘉时引用了她的导师和挚友对她的怀念,不是简单地叙述她的故事,而是要说她的率真,她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专业,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她有一种灵活的思维方式,她突破了过去阶级斗争给予人的思想框框,她在想问题的方式上和大家是不一样的,她视野很开阔、很会想问题。
另外,你们会看到,我用一章来写女性、讲性别。性别在原点上是平等的,没有后来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我要来证明的是男女平等。我花了比较多的工夫写了王尔德的《莎乐美》。为什么写《莎乐美》?那个剧最后的结尾是悲剧性的。那是唯美主义的写作,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凡是理想主义的、唯美的,就是自由的。审美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精神上的自由。在生活中,说这个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就是说这个人对自由精神的刻骨追求。有了这种自由的精神境界,才能有“死不回头”的风骨,才能不受那么多框架的束缚。我当时花了很多工夫来写《莎乐美》,就是要张扬一种追求自由的本性。我想可能有的人会说,沙老师的书里面写东写西写南写北,但实际上我这样写,都是想表达一个主题思想:“追求自由”是一种天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