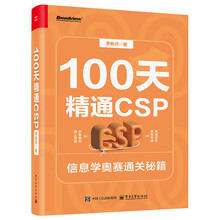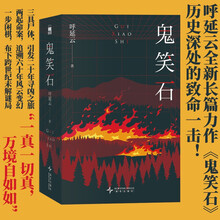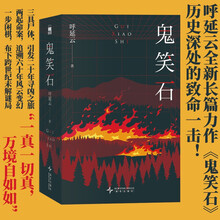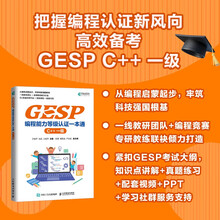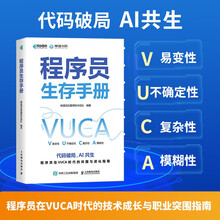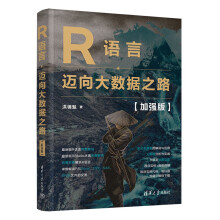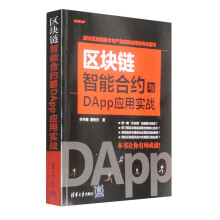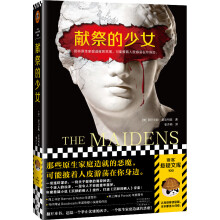《传播学的本土化探索》:
韩:您对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走向持什么样的观点?
邵:其一是科学化的趋势。传播学要想确立其与一些传统学科平等的地位,就要大力加强传播学的科学化建设。其科学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探讨传播规律的态势。我们知道,规律所在,科学所托。传播学若没有自己的明确对象和范围、从貌似紊乱无序的偶然现象中探寻出必然规律,那么它是不能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所以,积极探索传播规律应是传播学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二是积极构建理论体系的态势。传播学不是零星、杂乱知识的拼凑和剪贴,而是由一系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原理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知识体系。西方传播学界关于传播模式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其关注焦点仍是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预计关于传播学体系的探讨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走向开放,走向多元,走向普及,应是传播学研究走向繁荣和科学的基础。
其二是融合化的趋势。传播学大师施拉姆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讲学期间就做过大胆的预测: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经过综合都会成为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在这种情势下,传播学研究将继续发挥自己融汇、综合的优势。它不仅要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以不断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融合化趋势既反映了传播学者要对已有的知识和成果予以进一步系统的融化、整合的态势,又表明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强烈渗透和合理移植所采取的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
其三是鲜活化的趋势。未来的传播学要十分重视对活生生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即要特别注意观照和考察信息传播的动态过程,并注意着力解决传播活动中遇到的具体的实际问题,传播学研究不能抱着那些陈旧的资料不放,流于观点的引用和资料的堆砌,而应关注和研究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传播活动。活动是永恒的。现实的传播活动,既是传播理论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理论的实验场。离开活生生的传播活动,传播理论就会枯竭,就会窒息,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失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要关注鲜活的动态的现实,这也符合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其四是操作化的趋势。由于传播理论是对传播实践及经验的鸟瞰与把握,是一种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因而它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使某项传播在它的指导下能直奔某个预定的目标。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将从两个方面提出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传播建议或观点。一是依据传播规律提出传播对策。传播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传播活动的成败。传播者要求人们按照传播规律、联系具体实际,合理、科学地运用传播媒介、符号、谋略和技巧,使传播方法符合规律。二是通过分析传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传播问题,而受传者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接受问题,而传播学研究正是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
其五是分支化的趋势。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传播学也不例外。个别反对搞分支研究的人认为:传播学的分支研究会肢解基础研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传播学的基础研究和分支犹如心脏与血管、树干与树枝,它们相辅相成,互生互动,缺一不可。基础研究可以推动、促进分支研究,而分支研究也可以丰富、充实基础研究。
最后是本土化的趋势。传播学是“舶来品”,如果不同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吻合,不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生长出来,不与所在国家传播相结合并为其服务,而只是简单地贩卖和照搬,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本土化趋势,既不是一概排斥西方的传播学,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传播学,它实际上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本土化建设既可以增强其学科个性和民族特点,也可以推动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大众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因此,中国传播学只有针对中国国情,联系传播实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汲取营养,适应中国的社会特征、文化积淀和受众的心理态势、意识取向等条件,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才能真正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就可能是短命的。
韩:既然谈到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趋势,您可以谈一下对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的看法吗?
邵: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化”的研究上。对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反对,基本上不是“学理上的争论”,而是没有诉诸文字的某种“情感的宣泄”,传播学界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噪声”而不予理睬。实际上,在国内传播学界,本土化研究始终得到了大多数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支持。我认为,传播学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传播学有国界。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中国的尊“长”贵“和”、崇“礼”尚“忍”等观念也是“本土化”的。中国的传播学者的世界观、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因此,中国传播学研究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化”的全面渗透和强行框定;否则,那只能是对西方传播学的“照抄照搬”。
韩:在您看来,我们过去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有哪些特色?
邵:从研究过程看,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特色有:学科由窄到宽;论题由浅入深;范围由小到大;沟通由难到易;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国内的学术交流由封闭转为开放,由单向变为双向,由非正式变为正式,由交流发展为合作;研究人数由少到多,队伍由小到大,学者素质提升,并趋向年轻化。
从研究内容看,其特色主要有几点。一是纵向的寻根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已经或将要取得显著成果。除了赖江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 1978),吴东权的《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1988).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等著作之外,国内学者正在抓紧撰写出版一套中国传播断代史和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二是横向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和传播问题研究已经或即将获得长足发展。如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1993)和《沟通100: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 1997)、王洪钧主编的《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1998)等许多著作已经面世。预计在一两年内还将有更多专题论著和一大批论文出版和发表。三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其成果也很乐观。当然,这方面成果虽多,但在“中国特色”的认定上和具体著作的归类上,人们的看法还不一致,还需要历史河流的进一步冲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