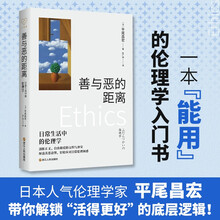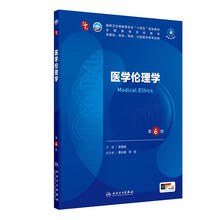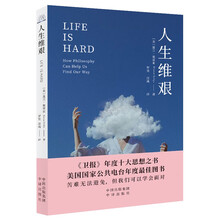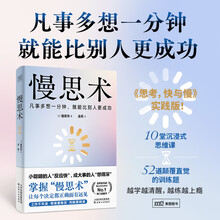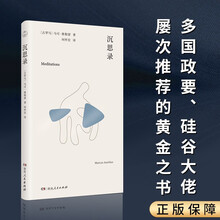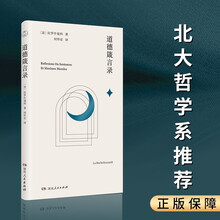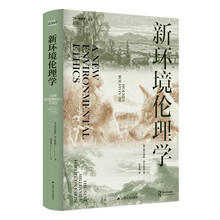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讲授“人格论”。在课堂上,希望大家重视两点:礼仪与名字。由于这两者与人格论并非没有关系,所以请允许我简单讲一下。大家在听完后,如果能明白我们的人格论课程不仅仅是能获得分数和学分的课程,我将十分高兴。
礼仪:不仅是一种限制
正确的行礼方式,是先低头,再抬头。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行礼了。可能有人会嘀咕:“不过是行个礼,至于这么严格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连行礼都不会的话,就更别说做其他事了。因为行礼的礼仪是当下正在消失的东西,所以我特别重视这一点。
虽然在现在看来,礼仪已是过时的东西,但我本人十分重视礼仪。因为我觉得礼仪与人性有很深的联系。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两个自己。在我们的心中,觉得“这么做更好”的自己和觉得“这么做太麻烦”的自己,觉得“不可以这么做”的自己和觉得“这么做无所谓”并最后做了的自己,经常纠缠在一起。既有觉得“不可以这么做”或觉得“必须这么做”的自己获胜的时候,也有因觉得麻烦而不做或觉得无所谓并做了的自己获胜的时候。如果要问在这之后是什么感受,我的回答是,大多数时候,即使觉得麻烦也去做的自己,比因觉得麻烦而不去做的自己更像自己。我想,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能表现出应有姿态的自己,和被各种欲望、需求所驱使的自己吧!
对人而言,欲望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但是,当欲望变成层次极低的欲望时,当原来的自己败给欲望时,我们不会有任何进步。久而久之,我们便会与猫、狗无异,便会变成想吃的时候吃、想睡的时候睡、想玩的时候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无能之人。可以说,让自己不做自己想做之事的人,以及劝自己做自己不想做之事的人,都是拥有自主性的人,都是拥有“我是自己的主人”的强大心理的人。
我觉得,生而为人的趣味存在于各种欲望、梦想、理想和现实的互相克制、互相纠缠之中。不过,败给欲望的自己,很无趣。礼仪之所以作为人性的一大表现而备受重视,是因为它很多时候都要求我们控制自己。即使觉得麻烦也让自己站起来,即使觉得麻烦也把手从口袋中拿出来,即使觉得麻烦也让自己和人打招呼。只要想讲礼仪,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就非常常见。
过去的修道院里,修女们必须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行动。比如:听到第一次钟响,起床;钟声再次响起,进教堂;钟声第三次响起,吃饭;钟声第四次响起,转到下个任务;等等。之所以说过去的修道院如何如何,是因为如今的修道院生活已变得非常自由,除了礼拜堂的钟声以外,再没有别的钟声。而我刚进修道院的时候,也就是距今30年前,修道院有很严格的戒律。钟声响起后,无论你正在看多么想看的书,你也必须合上书本,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再比如,你正在写信,写“木”字时才写到撇,这时钟声响了,你必须马上放下笔,去应该去的地方。这种训练,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非常痛苦,但今天再回头看,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钟声响起后,即使你觉得明明再读一行或读完这一页便能了解文章大意,即使某个字刚写到一半,你也必须立马停止。得益于这个规定,我拥有了自己劝说自己的机会。虽然我的这个经历有些过时,但我觉得其体现的原则在当下依然通用。因为它与时代无关,是一种让我们在该做什么时便做什么的训练。
在限制中,生活还是有更好的可能。
名字:自我同一性
除了需要重视礼仪外,我们还需重视自己的名字。
过去,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名字,有时甚至会想:“要是父母帮我取一个更漂亮的名字,比如‘小百合’之类的,不是更适合我吗?”但是,现在我喜欢上了自己的名字。某研究证明,人是否喜欢自己的名字与他是否接纳自己有关系。非常讨厌自己的人,也无法喜欢上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们的名字都不是自己取的,自己无法更改。所以,我们必须爱上自己的名字。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