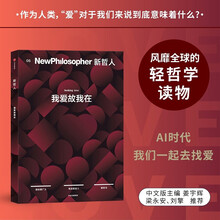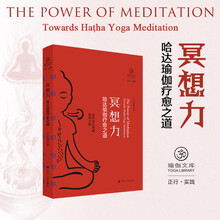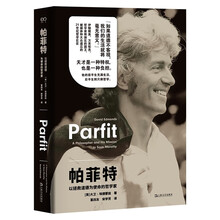也许由思想所呼吁的这些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梦想?自法兰克福末期起直到耶拿期间,我们看到在黑格尔那里有一种态度的完全改变。他不再想要改革实际的世界;毋宁说,他试图去理解并认识其中的一种必然命运。在后来关于历史哲学的讲稿中,他这样说:“倦于现实的各种混乱和直接的激情,哲学从中脱身出来以便委身于沉思。” 也许,这个极其宽泛的文本让我们见证了一种特殊的演变。我们可以询问,这种演变是在哪些历史影响之下完成的。它并不专属于黑格尔。在德意志,许多人都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但他们不久就不再理解它的进程了。1794年底,黑格尔已经向谢林表达了他对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血腥暴政的厌恶。共和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帝国军队发动的战争,已经使乌托邦主义者们开始反思。黑格尔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村庄毁坏过半,教会徒剩四壁。 最后,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观念开始显现。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Burke)的书已经于1793年由根茨(Gentz)译成了德语,它对于筹划中的那个浪漫主义的有机国家观念极其重要。 无疑,黑格尔像其他人那样经受了这种反动的浪潮,但他以自己的方式经受了它。他的新态度不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正是在他对于德国宪制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新立场的最明晰表述。在他看来,国家现在不再是一种契约联合的结果。它被强加给诸个体,就像他们的命运一样。正是通过强力,通过像法国的黎塞留(Richelieu)那样的伟大政治天才(而不是空论派)的行动,国家的统一才得以铸就。我们了解黑格尔就德意志帝国的处境所作的穿透性的和有时是预言性的分析,这个思想的国家是不可能支持对一族人民的决定性战争的。在这部作品中,[54]黑格尔宣称:“这部著作所包含的思想不打算有任何影响,它只想要让人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 如果说早几年前黑格尔还在颂扬“应然”(Sollen),那么他自此以后就建议要“理解实际存在的东西”,并由此揭示理念在实际存在的东西之中的必然发展了。然而,如果我们对此没有弄错的话,在这个表述中已经有一种音调,让人想到他未来的学生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现实主义了。 从一种改革者的态度到一种静观者的态度,从“应然”到“理解实际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前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重新看待其青年时期的所有主题和所有尝试的作品中,他要试图去理解那必然导向法国大革命的演进路线,以及他认为由此导出的同样必然的各种结果,这些结果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