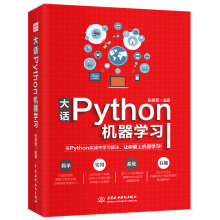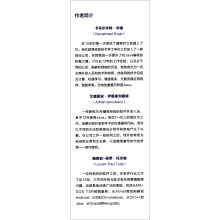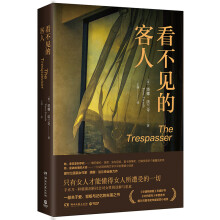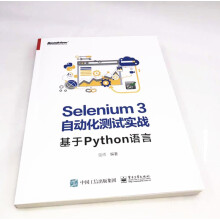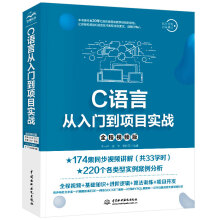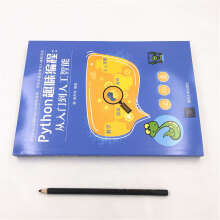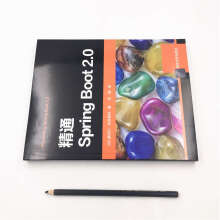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投资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中国经济在众多发达市场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保持了高
速的增长。不过可以肯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没有完结,中国经
济增长的潜力远没有释放殆尽。虽然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非常显
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正在改革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尽善尽美,本
章的研究显示,只要继续坚持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仍然很大。
之所以这么判断,可以从两点来分析:第一点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第二点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本章后面的实证研究将会表明,中国的
投资体制变迁确实导致了投资效率,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提高;
但是这种提高还存在缺憾,比如绝大多数金融资源还没有配置到效率
最高的地方或部门中去,这显然是一种配置扭曲,是效率不高的表现。
继续改进这种资源配置将会成为推动经济继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可以从不同部门和地区吸纳的劳动力
数量对比中看出来。我们本章整理的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金融资源
都配置给国有经济的同时,国有经济所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和速度却都
在下降,无论从相对量还是从绝对量上来看它都要低于非国有经济。
当然,正是这种资源配置结构也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资本
密集以及劳动密集的相对优势,因而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全面扭转这种
局面,但是,如果说金融资源与其相对应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比例过分
不协调的话,则对此我们需要改进。
正如张军(2003)所指出的,只要资本的形成还能够吸引并匹配更
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
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 年,中国经
济的资本密度发生了显著而快速的上升。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
经济而言,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密度的显著上升通常只有在
经济发展接近于充分就业之后才可能出现。而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几
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可见,这个提前出现的
“资本深化”现象的背后有体制上的原因。所以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是
一个需要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才能得到较好解释的现象。中国投资体
制的特征及其对中国资本形成效率的影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不
过,正如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
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的,它是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
互竞争的结果(张军,2002a)。这样的投资体制造成了改革以来中国
地方经济的投资结构和部门结构更加趋同而不是相反(Young,2000)。
总量投资远远高于在一体化的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Qin and
Song,2002)。由于过度投资,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从而赢
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而
显著的下降趋势。过度投资同时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袁志刚,2002),同时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尽管有不少文献揭示了中国投资体制的上述问题,不过,现有的文
第四章 实证分析中国投资体制变迁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49
献对改革以来中国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如
资本形成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
察。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分析中国投资体制对金融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特别是对稀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希望能够得出一些有启
发意义的结论,用来指导下一步的改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