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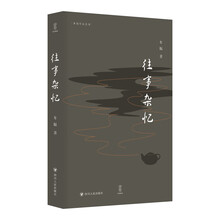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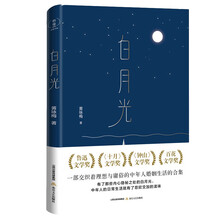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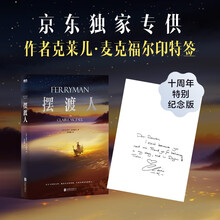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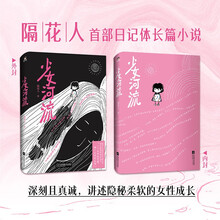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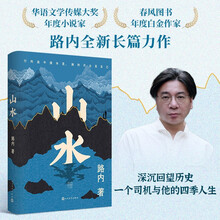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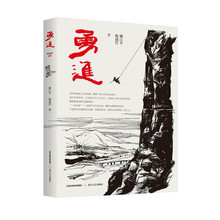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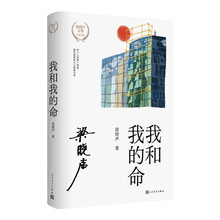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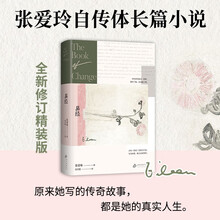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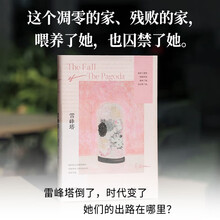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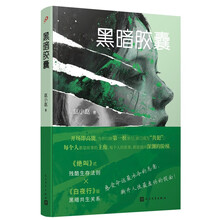
以细节铺陈生活的质感,每个人的人生都在寻找平衡
人生是一场飞行,保持平衡是最高境界,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平衡》以飞机平衡室的日常为故事背景,凭借细腻的笔触、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描写出以“家”和“职场”为空间的当代上海人生活的样本和哲学,提出每个人的“人生永远都在寻求某种平衡”,并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升腾起一种向上的力量。
故事在现实与梦境中蜿蜒前进,彼此缠绕
世间为幻,活即是梦。葛向阳是一位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的平衡高手,可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他的平衡能力却捉襟见肘,只能一次次借助梦境,寻求解开年少心结的方法。正如滕肖澜所言:“梦是现实的映照,每一缕气息都来自现实生活,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难言、一笔带过的东西,在梦里就被无限放大了。”人生中那些无法完成的遗憾,在梦中有了答案,梦也指向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沪爷沪姐高燃“反差萌”轻喜剧
浓郁的海派生活味道娓娓道来,细碎动人的沪上轻喜剧日常,让人在又哭又笑中掩卷深思。滕肖澜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运用时空转换、虚实交织的场景创造出梦里梦外的双重人格的“反差萌”角色。葛向阳的自黑、自嘲、自我解压,都能让处于快节奏生活中的当代读者会心一笑,故事里流露出来的危机感、梦幻感也增添了阅读的愉悦感。
为了凸显这次换课事件的隆重,我特意与葛小伟面对面谈了一次。我问他:“你很喜欢画画,对不对?”他点头:“对。”我说:“既然喜欢,那就好好学,认认真真地学。爸爸对你有信心,你一定会画得越来越棒。”
小家伙坐在甜品店里,吃做成小船模样的冰淇淋。嘴角一圈巧克力酱。我拿纸巾给他擦拭。触及他细嫩的肌肤,不知怎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佯装低头看手机。葛小伟说:“爸爸,我想玩会儿游戏。”我迟疑着,把手机给他。前几天我还批评华莉不该老是让葛小伟玩手机。现在却一脸满足地看儿子在那里娴熟地玩“消消乐”。还谄媚地问他“要不要再吃一个冰淇淋”。我看表,离约定把儿子送回去的时间还剩下20分钟。商场就在龙荣家对面,走快点10分钟应该足够了。如果我抱着葛小伟走,那还可以再快点,8分钟。我奔去柜台,又买了个冰淇淋回来。把手机收了,对他说:“少玩这个,伤眼睛。”他看着我,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回忆离婚前,我对葛小伟应该不会这么客气。当然也不太凶。就像大多数的年轻父亲那样,高兴起来玩两下,没劲了就随他去。男人在这方面确实不太有责任感。离婚是道分水岭。以前真没觉得葛小伟这么可爱。眼睛眉毛鼻子嘴巴,无一处不是美妙到了极点。连放个屁都悦耳无比,能跟着他一起傻乐半天。
20分钟后,我准时把葛小伟送回去。开门的是龙荣。他对我说声“谢谢”,又说“辛苦你了”。我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他问我:“要进来坐会儿吗?”我摇头:“不了。”把新买的一套画具递过去。龙荣没作声,看了一眼华莉。华莉道:“葛向阳你买这个干吗?”
我说:“给儿子画素描用的。”
“龙荣买过了,”她说,“跟你这套一个牌子,也是素描用的。”
我愣了愣,兀自不死心:“——我这套是正品,专柜买的。”
华莉斜了我一眼。意思是“你这人小儿科吧”。
“知道,”龙荣回答,“你这套是虎年礼盒款,专供国内的。我是托人从欧洲带的,普通包装,里面东西是一样的,铅笔、炭笔、木炭条……比国内专柜买稍微便宜点。”他笑笑,在我肩上拍了拍:“——破费了呵兄弟。”
我悻悻地捧着画具坐地铁回去。礼盒上那个红红的虎头,喜庆又可笑。我有些懊恼,不该拿回来的。葛小伟将来总归用得上。又不是吃的,会过期变质。而且从礼节上看,我是客人,客人不管送什么礼物,主人家都该充满感激地收下。这两人忒不懂事。华莉居然还问我发票在不在。我赌气说“丢了”。龙荣说:“没有发票也能退,把支付宝凭证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华莉加上一句:“实在不行你送人也行,现在到处都是学画画的小孩。”我板着脸:“我这是新年款,过了今年就送不出去了,不像龙荣那套,三五年后照样能送人。”
最后当然谁都没理我。葛小伟没心没肺地说了声“爸爸再见”,就被华莉推着去弹钢琴了。这小子吃冰淇淋的时候,完全没提龙荣已经给他买过一套,还不停地说“好看”。把我弄得很被动。男孩子就是这么戆头戆脑。不过也跟时代有关。我小时候应该不这样。会看山水是穷人家孩子的必修课。其实我父母的脾气性格还算不错,至少不像我和华莉整天怼来怼去。但境遇不能跟现在比。他们从崇明农场回来,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因为没钱。三十好几才有的我。我出生后的一两年里,我们与爷爷奶奶、叔叔挤在鸽子笼大的亭子间。那时葛胜还单身,街道居委会给他安排了一个看自行车棚的工作,专门值夜班。其实就是睡一觉。值班室有床和被子,夏天有风扇,冬天有油汀,算是条件不错了。既照顾了残疾人,也可以缓解我们家的住房难。我是完全没印象了,我妈还时常念叨,说那时多么艰苦,统共十平方米不到,除了一张床,再摆张折叠桌,走路也难。吃完饭便收起来,晚上打地铺,脚也伸不直。马桶在床角,拉个帘子略做遮挡。真正是一点私密也没有。
我自己盘算,那时是九十年代初,总体在走上坡路,似乎不至于如此逼仄。我妈回答:“就算是现在,也照样有人睡天桥底下。”——道理是没错,但一家子上海户口,都有工作,就算厂里效益差些,无论如何也还好。我妈的解释是,我爷爷是饭桶,除了我爸,另外两个孩子也统统是饭桶。“底子差,又没奔头,神仙也救不了。”那时候葛慧和刘新华还在恋爱,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而我爸也刚从崇明回来,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那是最艰苦的一段。1995年我爸聘上中级职称,没几年又分了房子。家里宽裕了不少。刘新华在圆珠笔厂上班,效益是越来越差,但他买认购证赚了一笔钱,如果不是葛慧人来疯发作,去澳门赌博一夜间输个精光,也许刘新华发迹还可以再早些。我奶奶常说,我家能走到今天这步,是靠了我爸和我姑父。我尽管听了很不舒服,但不能跟老人计较。我妈有时也会把我爸和刘新华放在一起评论:“你爸是读书人,你姑父是聪明人。”我说:“读书人未必不聪明,聪明人未必是好人。”于是我妈看我一眼,语重心长地劝我:“葛向阳你心胸可以再开阔一点。你是我儿子,我这么说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好。”
几天后,我又找了个借口把葛小伟接出来。打开一幅山水画,给他看。葛小伟不明白。我告诉他:“这是你太爷爷画的。”拿着他的小手点到落款处:“——葛辉民,就是爸爸的爷爷。你的太爷爷。”葛小伟很配合地叫起来:“哇,这么厉害啊!”
其实我爷爷这点水平,业余里的业余,也就只能骗骗小孩。关键是那份心性。我告诉葛小伟,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就跟现在厕所差不多大,到了晚上连灯也舍不得开,搬张小椅子当桌子,眯着眼跪在那里画。画几个小时,眼睛都成斗鸡了。这么艰苦的条件,太爷爷坚持不懈,每天都画到半夜才睡。这跟工作有关吗?无关。是为了卖钱吗?当然也不是。葛小伟问:“那他是为了什么?”我故意停顿一下,以表示接下去说的话郑重无比——“为了理想。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就算吃不饱穿不暖,也不能放弃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就算日子过得再好,那也不值得羡慕。”
给一个刚满五周岁的孩子喂鸡汤,我觉得挺滑稽。但面上严肃无比。让龙荣那厮去花钱如流水吧,买这买那,不是自己的孩子,他也只能这么干。我是亲爹,就要有亲爹的格局。物质是其次,关键是形而上的东西。儿子能否听懂也在其次。调子起得高些,后面再往下沉也是有限。我看着葛小伟。葛小伟在那里抓耳挠腮,搞不懂亲爹今天啥路道。就像二十年前的我。我爸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交给我,厚厚一本。我说:“看不懂。”我爸说:“看不懂才要看。否则你天天看《故事会》和《知音》,将来跟你姑姑一样,小市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你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弄不好也就是个中不溜秋。你要连个目标都没有,最后就像坐滑梯,一下子笃底了。”
据说爷爷当年也对我爸说过相似的话。我爷爷性格比我爸更温和些,运气也差,用我妈的话说就是“饭桶”。但如果没有我爷爷,我爸说不定也就只能当一辈子工人。我爷爷肯定没想过他儿子后来随便一个创意就可以卖350万。他之所以会画画,无非是出于对窘境的短暂跳脱,苦中作乐或是自我催眠。仅此而已。但到了我父亲那里,便将这种心绪落到了实处。要敢于做梦,要野豁豁。否则人生只能是一潭死水。据说我父亲调去当技术员时,家里人都有过疑虑。包括我爷爷。他们倒不是觉得技术员不好,而是在面对一个更宽广的陌生领域时,会本能地产生恐惧。毕竟往上数几代,都是抖抖缩缩过日子的。冒险也是要底气的。我父亲没理他们,径直去了。天赋加努力,让他在短时间内成为厂里最拔尖的技术员。几项专利,为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带来前所未有的效益。春节时,厂长甚至来我家拜年,激动地握着我爸的手,“葛工——”当时我在读小学,闻言差点笑出来。葛工偷偷朝我挤了挤眼,一只手绕到背后,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不管怎样,我爷爷喜欢画画,葛小伟也喜欢画画,这点非常好。现成的励志对象。很应景。万一葛小伟喜欢的是打高尔夫,那就麻烦多了。
“再拿爸爸画平衡表来说吧,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又搬出自己,“画平衡表是为了得到最佳的重心位置,让飞机在天上飞得又快又稳。但如果光为了重心,工作本身就会少了许多乐趣。换句话说,人工作是为了赚钱吃饭,这点没错,但如果工作就光是为了赚钱吃饭,那不是太没意思了?——所以爸爸在画平衡表的时候,没把它当成是工作,而是一种享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它带给我的乐趣,远远超过了工作本身。对我来说,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工作,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你明白吗?”
葛小伟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头。走题有时也能营造出一种影影绰绰的意味。我努力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鸡汤升华到了佛跳墙。我担心葛小伟会吃不消。虚不受补。但也没关系。从他的眼神里,我断定他被我震住了。这点很重要。要说服一个人,先要震住他。让他一头雾水,不敢乱说乱动。于是我语气更加柔和:“乖囡啊,爸爸就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说,爸爸不喜欢你,还会喜欢谁?”
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经常会说的话。通常前面说了过分(奇怪或是凶恶)的话,后面就会拿这句来缓和。小江说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小时候我妈也老说这句——我不喜欢你,还会喜欢谁?可问题是,‘喜欢’不见得都是对的,也要看怎么喜欢。长辈有时候就是这么主观,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没自信,拿这种话掩饰他们内心的虚弱。”小江说,“新闻里还报道过,有大冬天凌晨把儿子从被窝揪起来去跑步的爹妈,只准穿一件薄衣服,说起来也是喜欢,是为了锻炼身体。真不知道这是科学还是偏执。还有一不趁心就把孩子吊起来打,老法说是爱之深责之切,真是可笑。”
“还有买这买那,唯恐宠不坏孩子的,”我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龙荣,“说是喜欢,其实就是捧杀。”
龙荣没察觉:“三个大男人讨论这种话题,喜欢不喜欢的,腻心吧?”
我问小江:“你被你爸妈吊起来打过,还是大冬天揪起来去跑步?”
小江笑道:“我是被捧杀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