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庄》:
懂事的孩子都想为父母分担,梳草不满筐,那就不能回家。因为家家户户都需要叶子生火,所以离村子近的林里,便常常“寸草不落”,想完成任务,就得穿过一片又一片的木林。等竹筐满了,再踏着月光回家,幼小孩子的心里,都是满满的成就感。
捡干树枝也很重要,叶子是用来生火的,枝干可是最重要的烧火用的柴,所以除了掉下来的树枝不能错过,有些干枯在树上的枝干,也可以带上草格刀①割下来。不是干枯的枝干可不能随便乱割,只能由父母处理,而父母只能听从护林员老林的,逢年过节去老林家坐坐,叙叙旧,聊聊家常,其实就为了等老林一句话:
“你们家的木麻黄长得太旺了,可以去清理一下了。”
夏季台风频发,也是父母伤心而又忙碌的时节。每次台风一过,很多木麻黄被风刮倒,因为担心被其他人家顺走,父母常常冒着风雨,带上锯子,把一棵一棵倒了的木麻黄锯下,然后扛回家,再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堆在家里的角落,等太阳出来后,再晒干劈成一片一片的小木柴,然后整齐地堆在灶脚边。如果当年台风来了几次,那这一年储备的木柴也就可以用很长时间了,我们出外梳草捡树枝的任务就没有那么重了。
木麻黄可谓全身是宝!除了叶子枝干,木麻黄的根系发达,可以用来焖火炭。焖火炭其实也很简单,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把挖出来的树根直接点火烧起来,大概烧到五分左右,用沙子掩埋起来,几个小时后再把沙子清理开来,一个一个黑色的火炭就呈现在面前了。火炭也是农村人最重要的储备,因为家家户户的烘炉,烧的就是火炭,主要用于煮粥、炖汤、煎中药等。闽南的烘炉大多为红泥烧的,呈红色,分两层,上层放置火炭,有细孔,可通风,碳燃尽后灰烬也会从细孔中落到底层。每逢婚嫁、乔迁等日子,跨烘炉火是必不可少的礼仪。闽南人的除夕夜里,吃年夜饭的时候,桌子底下也要放一个烘炉,圈上红纸,烧上火炭,俗称围炉。
木麻黄也会开花、长籽,其花呈紫色,一到四五月,便一串一串挂在树上,甚是好看;七八月结籽,椭圆形,很硬很饱满,呈绿色,干后就成了黑色。小时候梳草,我常常在休息时和小伙伴追逐在丛林中,找木麻黄的籽当珠子玩,打闹时还用作攻击人的武器,因为有棱角,扔到头上可是疼死人了。
当然,与木麻黄的记忆,也是我们与这块土地最完整深刻的记忆,也是最天真烂漫的记忆。是木麻黄,给了我们这一切的美好,且不谈它固沙挡风的功能,单是它燃烧自己,给渔村人带来香喷喷的美食,就足够让人充满敬仰和怀念了。
从木麻黄林地再往大海的方向走,便来到一片坚硬的壳仔丁覆盖的地面。这种壳仔丁由大量贝壳和细沙经过多年风化作用而凝固一起,比石头还坚硬。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想到,用大锤把这些壳仔丁敲成一块一块,再一担一担挑回村里,盖起一落落独具闽南渔村特色的壳仔丁厝。记得父亲当年每次去海边牵网,总会挑一担壳仔丁回家,堆在家门前的平地上,以备日后盖房所需。这层壳仔丁被挖完以后,沙土再次露出地面,只是跟林地的细沙不一样,这些沙土粗大一些,一粒一粒的,太阳下还会折射出亮晶晶的光,晶莹剔透,像白花花的大米铺在地面上。
记得当时,奶奶每次到海边,总不忘感叹几句:
“这些白茫茫的沙,要是能变成米,我们就不用过苦日子了!”
没过多久,人们又发现,从沙土往下挖,深浅不一处,还有一层厚厚的贝壳层,足足三四米厚,五颜六色的贝壳,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数也数不清。以前在海边零星捡一些贝壳,主要用于玩耍,卖不了几分钱,可贝壳层储藏着这么多的贝壳,那可是能卖出大价钱的了。于是,村里人讨完海,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始了开壳仔、洗壳仔的日子。开壳仔就是用沙切①把沙土挖开,然后把贝壳一畚箕一畚箕地担回家。洗壳仔则难度大多了,因为有些贝壳层处于地下水层,人需要在沙丘上开出一个又一个的“壳仔窟”,然后泅水到深处,在贝壳层铲一筛子,再游到浅处站立,把筛子放入水中轻轻摇晃,细小的沙子被筛出去了,留下大的就是贝壳了。总之,不管开壳仔还是洗壳仔,担回村口的贝壳都能很快被卖掉,因为商贩每日都在村口等着收购呢。贝壳是制作石灰的最好材料,在离远庄村500米处的公路旁,就有一家烧灰厂,烧灰厂搭有两个长长的大土堆,跟坟冢差不多,上面常常冒着烟,怪吓人的。那时候每次从旁边走过,我全身上下都会起鸡皮疙瘩。
每一个壳仔窟都是海边人勤劳的见证。父亲当时也挖了一个,闲暇时就去洗壳仔。那时候,成堆成堆的贝壳就堆在壳仔窟旁,幼小的我们可玩疯了、玩腻了,后来对贝壳再也不感兴趣了。又过了没多久,贝壳层终于也被掏空了,留下了一座座白茫茫的沙丘,还有一处处越挖越深的壳仔窟。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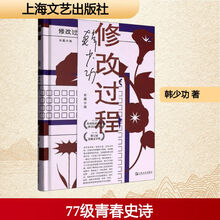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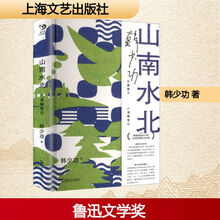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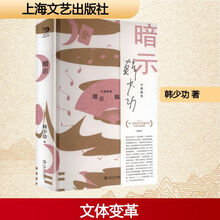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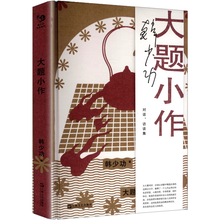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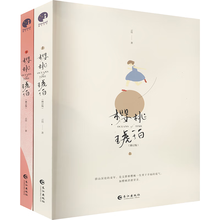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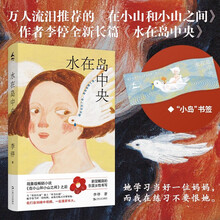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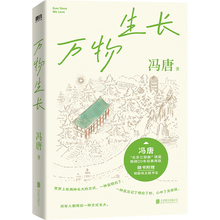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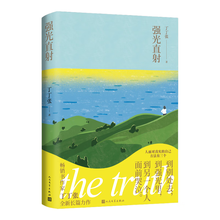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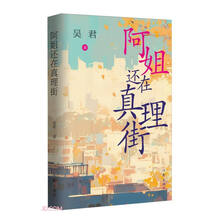
——刘原(专栏作家)
★《远庄》写满乡愁,笔笔流淌乡韵。曾经努力逃离,却是心灵家园。
——杨少衡(作家)
★《远庄》这部作品将会成为闽南文化乃至中国乡土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继续照亮后来者的心灵之路。
——吴尔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