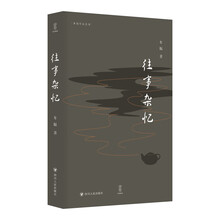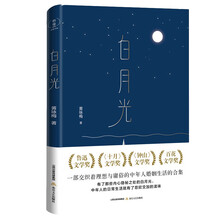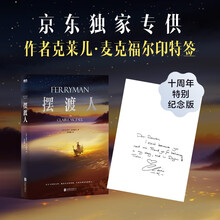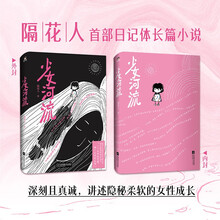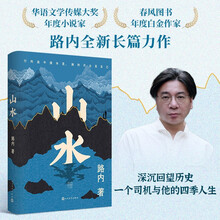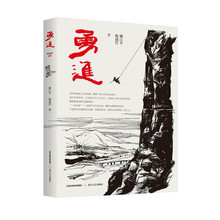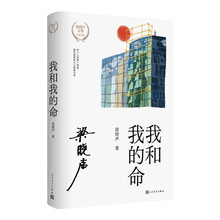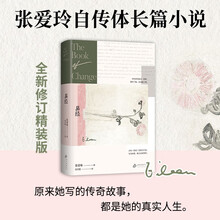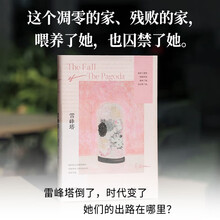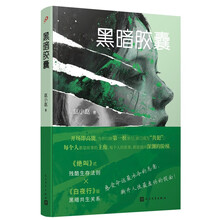《纵寒已是春寒了》:
很多年前读完樊锦诗先生的《我心归处是敦煌》,就开始对这个古老丝绸之路上璀璨的人类文明聚集地充满了向往。这次的大西北之行,沿着河西走廊,从嘉峪关到莫高窟,从莫高窟到鸣沙山,被历史的沉淀深深地吸引。丝绸之路从这里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张骞出使西域途经这里,卫青、霍去病痛击匈奴在这里,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时也途经这里……大漠,戈壁,黄沙中的声声驼铃,传唱的是只属于大西北的浪漫和经久不衰的故事。
当年,徐迟写了一部《祁连山下》,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敦煌莫高窟,如今的莫高窟早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来之前特地把有关樊锦诗、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的书籍重新读了一遍,直到自己踏进窟门,亲眼见到莫高窟里的彩塑、壁画和佛像时,才“不明觉厉”。伟大的作品总有一种令人泪流满面的力量,那些佛国世界、世俗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和丝绸之路的艰辛一笔笔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弹指间沧海桑田,一刹那转身千年。慨叹中国古代艺术辉煌和人类文明伟大的同时,蓦然间想起的就是那一代代为敦煌文物保护而将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的守护者们,他们也曾站在我们此时所站的位置上,一笔笔地为后人修复和镌刻历史。他们沉默但不寂寞,他们孤勇但不孤独。他们留下的是莫高窟千年的工匠精神——睁开眼是它们,闭上眼也是它们。几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地苍茫,岿然屹立于东方。
莫高窟啊,你是风吹不去的历史,沙掩不住你的光芒。
有人说,到河西走廊了,要敬三杯酒。第一杯敬张骞,第二杯敬霍去病,第三杯敬那些永远留在这里的汉家儿郎。自从张骞凿通西域、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以后,两千一百多年以来,这里有太多的文化积淀。河西走廊一带沦陷在吐蕃手里七十余年,后张议潮收复了沙洲,他派使者安排了十队人马从沙洲奔赴长安,告诉皇上这个消息,并把沙洲地图交给皇帝。这些人走到长安用了整整两年,最后仅存七人,其余人都命丧荒漠。如今,我们却可以自由地驾车穿越荒漠无人区,穿越河西走廊,那些人曾经奉献了生命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开放的景点。倘若当年也有现在的条件,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深埋于黄土之下。可历史从来都是向前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没有从前便不会有如今。也正是因为这些从前,才让这里成了一个充满神圣、盛满遗憾、镌刻不朽的地方。
眼里的河西走廊,纪录片里的河西走廊,书籍里的河西走廊,看得人热血沸腾。想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披荆斩棘十三年才从匈奴人的掌控中逃回来,鸠摩罗什被后凉王软禁了十七年才得以开始传经弘法……十多年,足以磨灭一个人所有的理想和信念,但张骞第一次出逃成功时想的并不是回到中原长安,而是继续西行完成他未完成的使命。当他寻找到月氏部落时,月氏并没有同意一起攻打匈奴。他还在回长安的途中再次被抓,又被扣押了三年,匈奴王死后他才回长安。出使时是二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的汉家儿郎,归来已形同邻家老叟,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壮举,更无法想象这是个信念何等坚定的人。
两千年前的塞外古道变成了现在的高铁轨道。时间再往前走,历史依旧在不断地交叠。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上,望见的是“新栽杨柳三千里”,辉煌而又苍凉。六十八岁的左宗棠在这里抬棺出征,抱着决绝的信念平定了疆乱,留下了大美千古的“左公柳”。汉朝的长城已经化为残土,打下的江山却永远属于中国的版图。那些悲凉、厚重、充满了热血的故事,依旧震古烁今,仿佛让人在今天还能听到沙场点兵、金戈铁马的雄壮豪迈。
那是一个浪漫和雄浑到了极致的时代啊!汉是天上的银河,帝国张开臂膀,使者凿空黄沙,将军的御酒倒入泉水和将士们共饮。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热血贲张、精力充沛的少年,强弓在背,利刃在腰,迎着大漠苍凉的风,马踏飞燕,扶摇直上。我们理应举起手中的酒杯,敬河西走廊,敬这片沃土上的汉家儿郎,敬中国历史的浑厚、宏伟与沧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