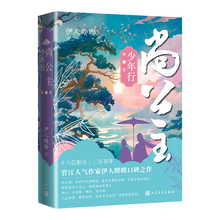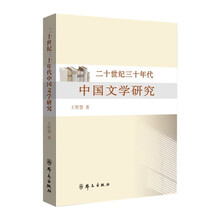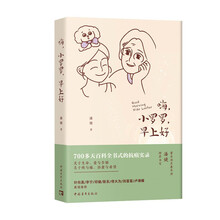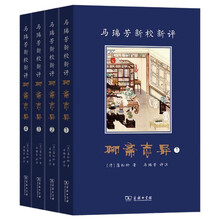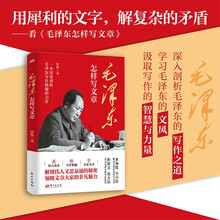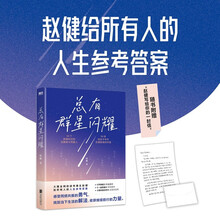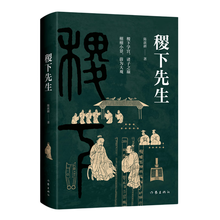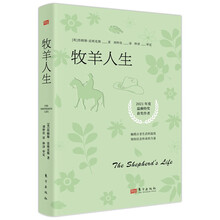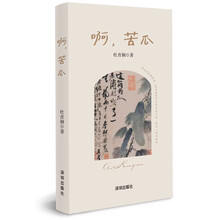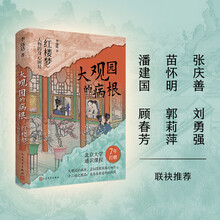按诗词经过历代的嬗变,每次都能推陈而出新。虽然有唐诗宋词这两座高山不得不仰止,但历代诗人都在求变,或者说求的是在前辈乔木阴影里寻觅到丁点立锥之地可容己身,或者从题材入手,或者从内涵着眼;而其中变化有成的无一不是贴合时代的作品。古典诗歌发展到当代,或多或少有些尴尬。因为失去了它可兹容身的土壤,它变得有些不伦不类,又显得有些迂腐,在大部分读者看来,它也仅仅成了小子内相互酬唱和比赛的文字游戏。殷千枝的古体诗词,也没法脱出这个时代的尴尬窠臼。它们小巧、伶俐、圆融,甚至可以称得上机智,但是由于其体裁限制,终归有一点不够转圆如意、稍有斧凿。而斧凿的谐音也即浮躁,这二者的不期而遇,应该也是时代的必然。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容不得合辙押韵的吟哦;但是诗人的热爱——对诗歌的热爱、对新时代的热爱,将这本来相互别扭的东西强扭在一起,这强扭的瓜还挺有滋味。类似描写梅雨天气的的“远山不见近楼灰,天地无形乳一杯”,戏谑的写实,又实则无奈。又如”折扇一支张使意,与君共解世人忧”,寓时政于俗语,格局大开而又典雅内敛。再如写瀑布,要写“崖前烟雨一白龙”,让人有莫名的熟悉感;再看“疑似鹰愁战悟空”,果然是个令人解颐的“用典”——这种典故与传统的文典不同,更类似于电影里的“桥段"或网络文化的“梗”,这也是这部诗集的某个侧面的新意,它不是有意安排的,它是作者包括我们读者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心有灵犀的东西,尽管无关社会的宏旨,但确是生活绕不开的作料——它不是我们的主粮,但是我们的油盐酱醋。当然,当代旧体诗词的不可避免的通病,这部诗集也不能免俗。比如过于追求音韵的准确而在字词的运用上失于灵活,泥于体裁的限制而在描写宏大主题上放不开手脚而略显匠气。当代旧体诗以聂绀弩为翘楚,它使得诗词从“载道”到“言志”“寄情”的脉络,直截了当地到了“抒怀”这一水到渠成的境遇。殷千枝的诗词也模仿或日继承了这一风格,语言不求典雅,但求合适,能适时、迅捷地表情达意是他在文字上的准求。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