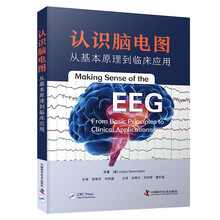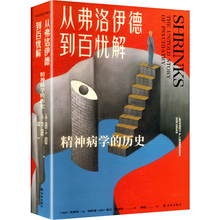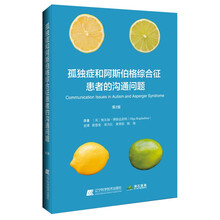我从没有结过婚,却要为离婚感到高兴。Ed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虐待我、控制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觉得我做得多么糟糕,以及我应该怎样做才对。我恨他,却无法离开他。Ed使我相信我需要他,离开他我就一文不值、一无所长,甚至变得更糟。他告诉我他总是在为我的最大利益着想——他那么做都是为了我好——而最终他却总是辜负我。他承诺,却从不守信。终于在我的身体和精神都跌落谷底之际,我决定跟他离婚。
让我多告诉你一些关于Ed的事情吧。他并不是高校的优等生,不是我在大学里开始约会的追求者,也不是我在超市付款台结识的人(尽管在关于超市的故事里他确实占了极大的分量)。Ed 的名字来源于eating disorder(进食障碍)开头字母的缩写,Ed就是我的进食障碍。
你可能会从内心里那些细小的声音中认出Ed来,听:“你只要再减掉几斤就好了。”“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卡路里吗?”Ed是那个从镜子里回望着你,并告诉你你的样子不令人满意的人。Ed会跟我们每个人交谈,有些人深深陷入与他纠缠不清的关系中,有些人只是偶尔跟他约会,也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遇见他。无论你是已经跟他结了婚,抑或只是调调情,这本书都是为你而写的。
我从心理治疗师Thom Rutledge那里学到一种治疗方法,可以与Ed也就是我的进食障碍彻底分开。在这种方法中,进食障碍被当成是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个体。在最初跟Thom的一次治疗中,他拿来另外一把空椅子放在我们前面,让我把它当成是我的进食障碍并对着它讲话。Thom没有在意我流露出的“你一定是疯了”的表情,继续说,“如果你的进食障碍正坐在这张椅子上,你会对他说什么?”好吧,他是专家,我又付钱请他为我治疗,那就试一试吧。我看着这把椅子说:“为什么你总想控制我的一举一动?你怎么就不能走开?”在问这两个问题的瞬间,我感到跟进食障碍拉开了一点距离,这种感觉真好。那次治疗里我一直继续与进食障碍进行这种交流,快结束时,我为自己的进食障碍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Ed(埃德)”,并且第一次感到自己向自由迈进了一大步。
与先前所有其他治疗结束后的感觉不同,那天,我离开Thom的办公室时,怀揣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在那次治疗中我感受到的那一点点与进食障碍分离的感觉,就让我相信自己有康复的可能。在与其他治疗师或医生的合作中,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分离的感觉。实际上,我常常在治疗时一直哭泣和诉说自己在康复尝试中的挫败,而在治疗结束后体会到更深的绝望,也就更深地陷入进食障碍。从没有人引导我积极地跟进食障碍去斗争。当然,有些专家也给我一些建议,但通常很不现实,也没有涉及真正的问题所在。例如一位精神科医生坚持认为,如果我回到学校上学,再拿一个音乐方面的学位,问题就能解决。他确信这样有助于改变我进食方面的行为。实际上,申请大学以及与入学咨询人员的交谈只是让我疲于应对,而无暇与进食障碍正面交锋。所以,你可以想象,当Thom给予我一种直接与进食障碍交谈的治疗方法时,我感到多么地解脱。终于能够把我的真实感受说给我的进食障碍听,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仅仅一会儿的工夫,Thom的治疗就让我重新找回了做Jenni的感觉——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她了。
与大部分接受这种治疗方法的人一样,我的进食障碍是位男士。这么多年来,在进食障碍治疗小组的所有姑娘们中,只有一个人感受到的进食障碍是位女士,她把“她”叫做“Edie(艾蒂)”。如果你的进食障碍也是位女士,你大可以用“Edie”替代这本书中出现的“Ed”,而重要的是要开始与他/她分离。
我用“离婚”来形容我与Ed的分离,是源于在治疗中了解到的一种类比方式,就是把我们与进食障碍的关系比做一段虐待性的婚姻关系,婚姻中的妻子被丈夫所控制,甚至施暴。身患厌食症或贪食症的女性害怕离开Ed就好像一个备受虐待的妻子不敢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样,因为那常常是她们唯一拥有和了解的东西。就像身处虐待性婚姻中的女性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总要隐瞒身上的青紫一样,身患进食障碍的女性也是这样隐藏自己的伤疤的。妻子们只有走出决心与虐待狂离婚的第一步后创伤才会开始愈合。这也是进食障碍患者在生活中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如果你从来没有结过婚,你可以把与Ed的分离看做是与男朋友分手,或者是与最要好的朋友决裂。再一次,请记住,最重要的是—分离。
在治疗中,我认识到康复不是消灭进食障碍,而是改变与他的关系。通过我的分离疗程,我与Ed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好像一对夫妇通过离婚的过程彻底改变关系一样。为了改变与Ed的关系,我必须学会抽身出来,主动与他分离。我得给自己的思想留出一定的空间,从而为表达与Ed不同的意见创造机会。我意识到,我对食物偏执的想法和对自己身体的否定与苛责都是来自Ed,而不是我自己。迄今为止,康复对我来说就是为真我的存在创造空间。
我对Ed的第一次记忆是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Ed在舞蹈课上嘲笑我是房间里最硕大的女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