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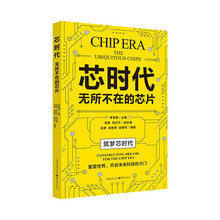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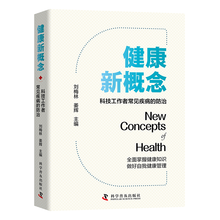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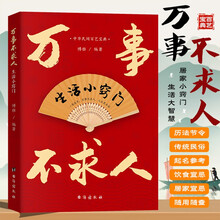






兰花是有特殊的魅力的花卉,中国人更是有着极强的爱兰情节。本书作者马克·A . 克莱门茨是澳大利亚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兰花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约二十五位画家以兰花为题材创作的一百四十多幅博物画,加上他关于兰花的高水平专业文字,向爱好兰花的人们生动而细致地展示了在澳大利亚这块植物新大陆进行探索的博物之旅
绘兰之技 在摄影技术和彩色胶片出现以前,要为动植物采像,唯一的方法就是绘画。 绘画让人可以一窥全球各地的新物种。几个世纪以来,兰花让无数文人墨客神思泉 涌,因为兰花的花型可谓复杂多样,千奇百怪。 卡尔·林奈命名了兰花——Orchis。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睾丸”,林奈 是依照生长在希腊牧场上、拥有新、旧两个睾丸状块茎的兰花种类,来为整个兰花 类群定名。林奈通过描述与识别动、植物特征的方法,确定了所有现代植物学的范 式。如今,虽然仍有一些植物学家认为,用文字描述新物种就已足够,但通过细 致、准确的插图来呈现新物种确是植物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18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家都非常热衷于绘制澳大利亚的兰花。受欧洲航海 大发现的驱动,艺术家也加入了航海船队。他们的素描和油画不仅记录和报告了某 些事件、行为和地点,还呈现出了他们所观察到的动植物。这些动、植物画作既有 整体草图,也有细节剖面图,质量参差不一。它们不仅是艺术品,也是重要的科学 文献。很多早期的欧洲艺术家绘制动、植物,都带着对母国熟悉物种的怀念之情。 也有一些动、植物画作笔法精细,色彩缤纷(通常以水粉绘制),其中就包括了 兰花。
1768—1771年,詹姆斯·库克上尉在第一次航海途中,观测了金星的运行,而 博物艺术家悉尼·帕金森也在“奋进号”(Endeavour)上。这是一次重要的科学 发现之旅,为了实现目标,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和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携 带了20吨设备。这次航行条件艰苦,空间尤为宝贵。仅管如此帕金森还是绘制了三 幅关于树生兰花的重要画作——弯刀石斛(Dendrobium)、细管石斛(D. canalicu latum)和异色石斛(D. undu latum)。帕金森在“奋进号”上绘制的草图,是“奋 进号”在奋力河(现在的库克敦)维修时绘制的。后来,这些画作被班克斯的学 生、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引用。1810年,布朗用科学语言描述了这些新发 现的品种。 新殖民地艺术家的出现,始于约翰·亨特船长和他的见习船员乔治·雷珀。 两人于1788年登上了第一舰队的“天狼星号”(HMS Sirius)。约翰·亨特是阿 瑟·菲利普船长的副手,菲利普船长曾做过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首任总督,他自己 将成为第二任总督。在亨特素描本《1788、1789、1790年新南威尔士本地的花鸟》 中的众多水彩画中也包括了少量兰花。这些极富个性的画作,用色不多,显示出他 并未经历过科班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清晰描绘出了金色双 尾兰(Diuris aurea)、大蜡唇兰(Glossodiamajor,后更名为Caladenia major)和斑 点柱帽兰(Theiymitra ixioides)的明显特征,说明这些品种曾经随处可见,但现在 只在悉尼郊区生长。乔治·雷珀也未经过专业训练,但他的画技进步神速,很快就 成了第一舰队所有科学画师中最有天赋的一位。在雷珀的众多画作中,有一幅准确 描摹了斑唇双尾兰(Diuvis punctata),这是一种当地的原生兰花,花朵如紫丁香般 绚丽。 职业画师费迪南德·鲍尔是当时最杰出的植物画家之一。鲍尔搭乘马修·弗林 德斯的“调查者号”(Investigator),于1801—1803年展开了环澳大利亚之旅。鲍 尔在返欧途中绘制的水彩植物画,被保存在伦敦肯辛顿的英国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ny Museum)的植物馆里。这些作品如今都完好地收藏在特制的匣子里。20世纪80年代,作为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dens, Kew)——的访问学者 和科学家,我在自然博物馆研究了鲍尔的画作。我带着笔记本,戴上白手套,花两 天时间精心翻阅了鲍尔画夹里的每一幅澳洲兰花画作。这次经历收效甚佳,凭借画 作对实物近乎完美的描摹,我可以确定很多兰花的学名。鲍尔的画作对兰花颜色和 比例的准确呈现令人震惊,他呈现兰花的方式也颇有创意。和其他船只一样,“调 查者号”上的空间和绘画材料也十分有限。鲍尔的原作均以铅笔绘制在尺寸不等的 小张粗纤维纸上,就夹在他那些保存在博物馆的插画藏品里。一种兰花往往有数幅 素描,每种植物的颜色、花朵部分和剖面都以一种色码标识,以便后来绘制水彩 画。每一张插画画的都是一个特定的种,鲍尔时常试画上两三幅,才会满意。 我们很庆幸,费迪南德·鲍尔和弗里茨·鲍尔两兄弟开始绘制这些画,并在 早期绘制了很多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植物。通过他们的精准描摹,我们可以判定这 些物种究竟是什么,并在重要出版物中描述并引用他们的画作。罗伯特·布朗的经 典作品《新荷兰岛范迪门植物群的历史》(Prodromus Florae Novae-Hollandiae et Insulae Van-Diemen,1810)也经常被人引用,描绘了他在澳大利亚之行发现的许多 植物。他的文字叙述用词简单,用的是拉丁语,旨在和鲍尔的作品一起拉开对澳大 利亚植物群更细致综合的描述的序幕。但学界对布朗的拉丁语褒贬不一,让布朗倍 觉侮辱。于是,他撤回作品,不再售卖。因为拉丁语通常较为简洁,有时候两个物 种的区别只在一个单词,所以图画就十分重要了,因为图画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株 植物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丰富的新物种画作,那么所有后继的植物学家都会倍感 纠结,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将布朗的命名与合适的物种对应起来。 描述兰花物种的异同,或识别各个种的特征,以便与其他兰花比较异同,是 寻找和研究兰花的主要动力。我们许多前辈植物学家和画师都想知道,当他们第一 次来到兰花之国,接触到这一类植物,究竟是何种魅力打动了他们?虽然澳洲本 土的兰花属种并不多,大多数典型的澳洲物种都集中分布在澳大利亚,当然还有 一些物种生长在周边国家——尤其是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但那些著名的兰花物种,如裂缘兰属(Caladenia)、胡须 兰属(Calochilus)、双尾兰属(Diuris)、韭兰属(Prasophyllum)、翅柱兰属 (Ptrrostylis)、柱帽兰属(Theiymitra),还是集中分布在澳大利亚。 1791-1794年,法国探险家布鲁尼·德·昂特勒卡斯托抵达澳大利亚,随行 的植物学家雅克·拉比亚迪埃在塔斯玛尼亚岛和西澳大利亚的西南部采集了丰富 的植物标本。其中就包括五种兰花,后来收入他的《新荷兰植物观察》(Novae Hollandiae Plantarum Specimen,1804—1806年在巴黎出版),这本书也是当时对澳 大利亚植物的最全面的记录。皮埃尔-安托万·普瓦托和皮埃尔-约瑟夫·勒杜泰两 位画师也受雇于法国政府开始绘制植物,他们绘画的很多作品是由奥古斯特·普莱 和维克图瓦·普莱父子俩刻印的。 很多澳大利亚兰花品种在首次描述时,都会采取如拉比亚迪埃等植物学家们 更为熟悉的命名方式,甚至绘画模式也是如此。这并无惊奇之处。比如,具翅翅 柱兰(Pterostylis alata)在《新荷兰植物观察》中第一次出现,就被描绘成双袋兰 属(Disperis),而这是一类主要在非洲生长的兰花物种。画师们对于不常见的兰 花的种也不甚熟悉,比如,同样在《新荷兰植物观察》中,反曲飞鸟兰(Chilogttis reflexa,曾被命名为Epipactis reflexa)就被普瓦托绘制成了在唇瓣上没有胼胝组织 (一种凸起结构)特征的一种花,当时普瓦托认为是植物学家错把一只蚂蚁当成了 花。用这样的方式描绘反曲飞鸟兰,画师就在无意间除去了识别这一物种的关键性 鉴别性状。所有的飞鸟兰种类都具有典型的唇瓣胼胝组织,模仿了一种特别的磁性 无翼黄蜂。有翅膀的雄蜂误将这种兰花当做雌蜂交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兰花授 粉。幸运的是,考虑到这种兰花是在塔斯马尼亚岛采集的(并考虑到其他植物鉴别 性状和花卉鉴别形状),飞鸟兰是这幅图画指代的唯一可能的兰花品种。这个例子 的确有些可笑,但也说明了早期欧洲植物学家在澳洲所遇到的困境。 费迪南德·鲍尔返回欧洲后,在澳洲这片发展中的殖民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兰花画家,他们身份各异,难以一言蔽之。
绘兰之技 / 1关于兰花 / 15兰花 / 22地生兰 / 25附生兰 / 115画家小传 /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