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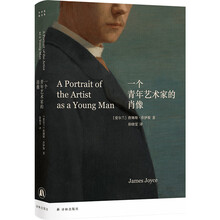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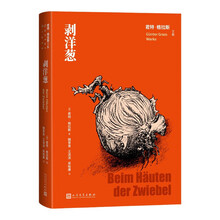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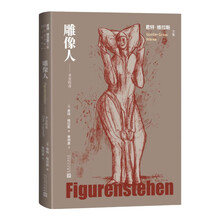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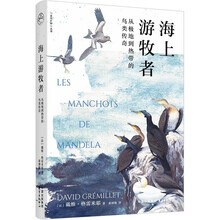

★诺奖得主帕慕克的诺顿演说集
★充满内心情感、富有灵魂气息的小说鉴赏指南
★自如穿梭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卡夫卡等小说大师之间的精妙解读
“我在年轻的时候阅读小说时,有时内心会出现一片宽广、深远而又宁静的景观,有时光线暗淡下去,黑白分明并且相互分离,各种阴影在其中涌动。有时候,我惊诧地感到整个世界沉浸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光芒之中。有的时候,余晖普照,含摄一切,整个宇宙化为唯一的情绪和唯一的样式。我知道,我爱上了这种感觉,我在书中追求的正是这种特别的氛围。”
本书汇集了帕慕克在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讨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创作历程,小说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小说对于读者产生效果的方式等等这些话题。书名来自席勒对两种不同文学风格——“天真的”和“感伤的”这一的经典区分。帕慕克在与席勒文学观念的对话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小说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小说创作就是要在那种直观的、朴素的天真与反思性的、解构性的感伤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帕慕克还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观点,即现代小说与古代的文学(比如史诗)所不同的是,小说必须拥有一个中心,而书中的种种细节都应该指向这个中心,这个中心也就是可以在阅读中慢慢靠近和体验到的小说的意义,或生活本身的意义。
词语,图画,物品
我说过写作小说的艺术在于具备一种能力,可以从一片景观之中——也就是说在物品和意象的包围中——感知主人公的各种思想和感觉。这种能力对于有些小说家显得并不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有时候感觉遇到了某种极为深刻的东西——我们获得了一种有关生活、人,并且首先是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知识看起来如此熟悉,同时也如此非凡,偶尔使我们内心充满恐惧。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给我们的知识或智慧不是诉诸我们的图画想象(visual imagination),而是诉诸我们的词语想象(verbal imagination)。说到小说的力量和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尔斯泰有时候同样深刻。因为这两位作家来自同一时代和同一文化,人们总是拿他俩比较。然而,托尔斯泰的洞察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察力在主要方面是不同的。托尔斯泰不仅诉诸我们的词语想象,而且——甚至更多地——诉诸我们的图画想象。
每一个文学文本无疑都会同时诉诸我们的图画智能和文本智能。在实时上演的剧场里,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为我们带来视觉享受、语言游戏、分析思维的快乐以及诗性语言的乐趣。日常语言的流动当然也是我们快乐的一部分。说到高度戏剧化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说,《群魔》中的自杀场景——纸面上或许并没有明确的意象(读者必须跟随主人公想象某人在隔壁的房间自杀),然而那个场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可是,尽管充满了让读者头晕目眩的紧张感——或者因为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粘连在我们意识中的实际上只有少数的物品、意象和场景。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世界充满了富有暗示性、巧妙安排的物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舍看起来几乎是空空荡荡的。
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一些概念,以便更轻松地解释我的观点。有些作家更擅长诉诸我们的词语想象,另外一些作家则更有力量诉诸我们的图画想象。第一类作家我称之为“词语作家”,第二类作家我则称之为“图画作家”。对我来说,荷马就是一位图画作家:当我阅读他的著作时,无数意象在我眼前穿过。我喜欢这些意象甚于故事本身。但是伟大的波斯史诗《列王纪》的作者菲尔多西则是一位词语作家,我在写作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时曾阅读过他的著作,他主要依赖情节以及情节的各种扭结和转向。当然,任何作家都不能完全归为上述区分的一边。实际情况是,当我们在阅读有些作家的时候,我们更加专注于词语,专注于对话的进程以及作家正在探索的种种悖论或思想;而另外一些作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纳入不可磨灭的意象、想象、景观和物品。
有的作家既可以是图画的,也可以是词语的,依使用的体裁而定。柯勒律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的诗而论——例如,《古舟子咏》——他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为读者绘制一系列璀璨的图画。但是在他的散文、个人日记和自传里,柯勒律治就变成一位分析性的作家,希望我们可以完全以概念和词语思考。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洞烛幽微地描写自己如何创造诗:他以图画想象写诗,同时又以词语想象分析诗——见他的《文学传记》第四章。埃德加·爱伦·坡从柯勒律治受益良多,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其论文《创作的哲学》中解释自己的诗作《乌鸦》,手段就是诉诸读者的文本想象。为了理解我称之为“图画文学”和“词语文学”之间的区分,让我们暂时闭上眼睛,将思维聚焦于一个主题,让思想在我们意识中成形。然后让我们睁开眼睛,反问自己:在我们思考的时候,什么穿过了我们的意识——词语还是意象?答案可以是任何一个,也可以是二者兼有。我们感到,我们有时候以词语思考,有时候则以意象思考。我们经常从一种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方式。现在,我打算通过图画和词语之间的对比,说明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学文本总倾向于在我们脑海里调动某一中心,而不是其他中心。
以下是我最坚定的观点之一: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文学虚构。通过诉诸我们的图画智能——我们在心目中观看事物并将词语转化为内心图画的能力——小说对我们施加最主要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依赖于我们对普通生活体验的记忆以及有时候会被我们忽视的感觉印象的记忆。除了描绘世界,小说还描写——以一种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匹敌的丰富性——我们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所激发的感受。小说的总体景观——超越主人公们所看到的——透过那个世界的声音、气味、味道和发生接触的时刻变得鲜活起来。然而,在我们每一个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实际获得的体验之中,视觉无疑是最重要的。写作小说意味着用词语绘画,阅读小说则意味着通过别人的词语具象化种种意象。
所谓“用词语绘画”,我的意思是通过词语的使用在读者的意识中激发出一个清晰鲜明的意象。当我逐词逐句(除了对话场景之外)写作小说时,第一个步骤总是在我的意识中形成一幅图画、一个意象。我知道,我的直接任务就是阐明这个内在意象并将之带入焦点。通过阅读传记和作家的回忆录,通过与别的小说家交谈,我逐渐认识到——相比于别的作家——我在动笔之前花费更多精力用于规划。我小心翼翼地把一本书分成许多章节,将之组成一个结构。我在写作一章、一个场景或一个小场面(你看绘画术语自然地就来到我的笔下!)之时,首先以心灵之眼仔细将之观看。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具象化那个特殊场景、那幅图画的过程。我抬头眺望窗外和我低头注视自来水笔书写于其上的纸张,两个动作同样重要。当我准备将思想转化为词语的时候,我努力像过电影一样具象化每一个场景,并将每一个句子具象化为一幅图画。
但是电影和绘画的类比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当我准备描写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努力想象和凸显其外观,用最简洁有力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在我的图画想象一句接一句、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构造笔下的章节之际,它聚焦于那些最能被有效地用词语表达出来的细节。有时候,我回想起实际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并将之具象化为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知道自己不能用词语将之表达出来,我就会放弃这个细节。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是由于我相信我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我搜寻着“恰当的词语”——福楼拜在写作时也如此搜寻(事实上,他在坐下来写作之前就已经这么做了)——以便充分传达我内心的意象。小说家不仅寻找那些能够最好表达其图画想象的词语,而且也逐渐地学会如何想象其善于用词语表达的事物。(这样一个精心选择的意象应该称作“恰当的意象”[l’image juste]。)小说家认为,自己在心灵之眼中看到的意象只有转化为词语才能获得意义,并且大脑里图画中心和词语中心越靠近,他将具象化的事物重铸为词语的能力就越强。这两个中心也许是一个安居在另一个内部,而不是位于头脑中相对的位置。
每当谈论词语和意象之间或文学与绘画之间的亲缘关系,人们通常会引用贺拉斯《诗艺》中“诗歌就像图画”(Ut pictura poesis)这句名言。我还喜欢这句陈述之后的那些不太知名的言论(贺拉斯说的这些话出人意料,他甚至宣称荷马也可能创作低级的诗行),因为这些话让我想到看一幅风景画与阅读一部小说非常相似。这一段话是:“诗歌就像图画:有的要近看才能看出它的美,有的要远看;有的放在暗处看最好,有的应放在明处看,不怕鉴赏家敏锐的挑剔;有的只能看一遍,有的看十多遍也不厌。”
贺拉斯在《诗艺》的其他部分也使用了绘画的类比和词汇,但是他的这些观念和例证只不过提及诗歌给人的快乐与绘画给人的快乐相似。文学与绘画艺术之间的真正区别是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在《拉奥孔》(1766)中通过逻辑分析提出来的。该书以《论画与诗的界限》为副标题,阐述了如今所有人都认同的区分:诗(文学)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而绘画、雕塑和其他视觉艺术是在空间中展开的艺术。时间和空间是康德哲学的核心范畴。
观看一幅风景画,我们立刻就会抓住总体意义:所有事物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要抓住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叙述的总体意义,我们必须理解主人公和环境如何在时间流转中有所改变——换言之,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故事、场面和事件。事件依托于戏剧化时间的氛围中。为了理解其结构,我们需要花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欣赏一幅细节丰富的风景画,我们必须——如贺拉斯所言——看上十遍,关注细节,从不同距离将之打量,花时间仔细琢磨。不仅如此,那种呈现故事的绘画能够在单个画框里容纳多种时间——我在上一讲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时刻。在一幅大型绘画的一角也许描绘了一起引发一场大战的事故,而另一角也许会呈现此次战争之后留下的伤者与死者。这种绘画我们称为“叙事画”,其技法见于16 世纪早期,如欧洲大师卡尔帕乔(Carpaccio)和同一时代的波斯大师贝赫扎德(Bihzad)。
但是,这些例子并不有损于莱辛所做著名区分的有效性。他所使用的两大哲学范畴,时间与空间,在诗与画(常被称为“姐妹艺术”,因为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的感染人类心灵的力量)之间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对比。让我利用这个区分表达我自己关于小说的观点。小说就像绘画一样呈现凝固的时刻,但它不会只包含一个这样微小的、无法分割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式的时刻):会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时间点。阅读小说时,我们具象化这些由词语构成的时刻,这些时间点。也就是说,我们将它们转化为想象中的空间。
我们观看一幅绘画时——无论是风景画、书的插图、草图手稿、人物肖像或静物写生——直接就得到一个总体印象。但是阅读小说时情况却截然相反。我们翻动书页时,我们的注意力一直聚焦于小细节、小画面、不可缩减的微小时刻,努力记住无数细节,即使不耐烦也需要坚持,最终才能够构想出总体景观。如果说绘画呈现给我们一个凝固时刻,小说则呈现给我们成千上万个、一一前后相续的凝固时刻。阅读小说的过程通常充满悬念,我们的好奇心急于要确定每一个时刻与总体景观的吻合之处,而且它又如何指向小说的中心。为什么作家要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向我们呈现窗外的雪花?为什么他要提供关于车厢内其他乘客的细节描述?在浩瀚的时刻森林之中追问我们身在何处或者如何才能找到出口——同时还要检查每一棵树、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叙述单元——也许会令我们感到窒息,就仿佛我们完全迷失在树林里一样。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会松懈,因为森林里的树木、成千上万个构成故事的无法分割的细节来自普通人的生活并且通常是图画性的。这些能够抓住我们注意力的细节也正是它们向主人公呈现的样子——换言之,它们揭示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
面对一幅大型画作,我们因所有事物同时尽收眼底而感到激动并渴望进入画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之中,我们会因为置身于一个无法一览无余的世界而感到眩晕的快乐。为了看到所有事物,我们必须不断将离散的小说时刻转化为意识中的图画。这个转化的过程使得阅读小说比起观赏绘画更具协作性,也更加个人化。
我和朋友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联合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个研讨班。该课程旨在探索文学文本和绘画之间的关系,通过实例讨论词语如何调动我们的图画想象。我们在讨论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古希腊人称之为描绘(ekphrasis)的概念。该词的狭义和首要意义是指通过诗歌表达的手段描写视觉艺术作品(如绘画和雕塑),为那些无法观看的人提供帮助。诗歌中的绘画和雕塑可以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就像小说里的细节。这实际上就是该词的全部意义。古典文学里最有名的描绘实例是《伊利亚特》第十八卷关于阿喀琉斯盾牌的描写。冶炼之神赫菲斯托斯将许多形象——星星、太阳、城市和人民——铸入了阿喀琉斯的盾牌,荷马对此给予了不同凡响的描写,用词语囊括了整个大千世界,其文本比那个盾牌本身更加重要。W. H. 奥登受到了荷马描绘的启发,将一首诗命名为“阿喀琉斯的盾牌”,从20 世纪战争的角度重新塑造了描绘的概念。
1 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 ......... 1
2 帕慕克先生,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 31
3 文学人物,情节,时间 ......... 57
4 词语,图画,物品 ......... 87
5 博物馆和小说 ......... 121
6 中心 ......... 153
收场白 .........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