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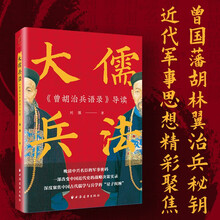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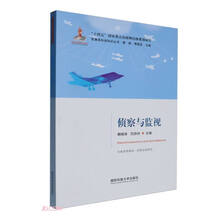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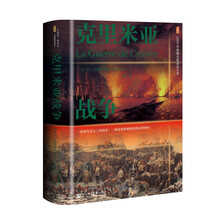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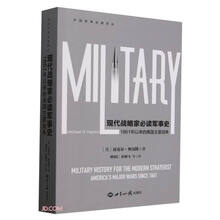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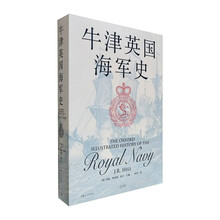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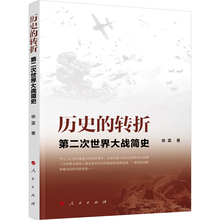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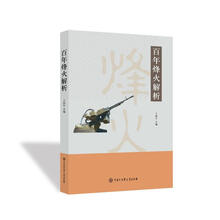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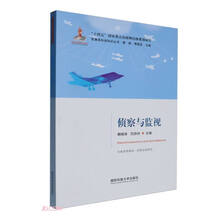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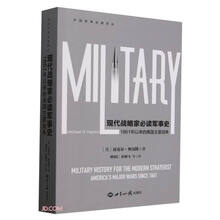
一位退伍军人向他的孙子讲述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没有夸夸其谈,只有扣人心弦、残酷的诚实。
本书整理并讲述了汉斯·卡尔(Hans Kahr)对二战东线战场的战后回忆和战时记录。
汉斯·卡尔1925年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被征召入伍,成为德国国防军第3山地师第138山地猎兵团的机枪手,在战争后期被派遣到东线战场。书中回忆了汉斯作为新兵在前线学习生存的过程,讲述了汉斯在东线战场残酷的战斗,以及被俘后作为战俘的经历。书中还介绍了战前奥地利小农家庭的生活和当地传统习俗等。
本书整理并讲述了汉斯·卡尔(Hans Kahr)对二战东线战场的战后回忆和战时记录。
书中没有很激烈的语言,从一位普通士兵的角度,将战争的残酷一一展现,留给后人的是警醒和珍惜。
1943年12月19日,我经受了战火洗礼,这场激战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切都不同了。面对恐惧和精心安排的大规模杀戮,我这个年轻人的无忧无虑彻底消失了。我们的二级下士无疑也知道。我傍晚下岗后返回掩体,他拍拍我的肩膀,掏出个饰有雪绒花的破旧扁酒瓶,倒了杯杜松子酒递给我,以父亲般的方式对我简短地说道:“您今天打得很好,会习惯的。”
就连我这样的新兵也知道敌坦克为何要竭力控制主要补给路线,因为这条道路穿过第聂伯罗夫斯卡和沃加内,直通第聂伯河渡场。第聂伯罗夫斯卡基本上是个贫穷、遍地泥泞的草原村庄,我们的前进补给点和几个指挥所设在村内。严冬这几个月,第3山地师官兵眼中的宇宙中心就是第聂伯罗夫斯卡村,我们的性命取决于能否守住该村。要是敌人攻占第聂伯罗夫斯卡村,就切断了我们身后的交通线,我们只能分别跨过寥寥几座临时搭设、通往河北面的桥梁。这些桥梁不是为快速后撤设计的,更别说用于整支部队的退却了。我们在圣诞节前经历的激烈交战,接下来几天和几周多多少少会持续下去。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4年1月1日发布公报,谈到我们这片作战地域的情况:“苏联人实施了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坦克和战机为支援,重新对尼科波尔登陆场发动进攻。德国军队以大规模反突击击退敌人。敌人损失惨重,大批坦克遭击毁。”
苏联人的进攻很快成为常态,但我们确信,只要弹药充足,第24装甲师在身后提供支援,我们就能应对一切状况。至于口粮,我们班不得不派一两个士兵,借助夜色掩护赶往卡缅斯克,替班里的战友把饭盒打满。
有一次轮到我去打饭,途中看见许多阵亡的山地兵躺在道路两侧,身上盖着防水帆布。他们可能是在争夺第聂伯罗夫斯卡村的战斗中牺牲的。凛冽的寒风把帆布吹得噼啪作响,帆布卷起,我看见尸体上可怕的伤口。一具具尸体面目全非,几乎难以辨识,没了四肢,胸部和腹部的弹孔很大。我当时暗自思忖,他们至少死得很快,没遭太大罪。
在另一次去打饭的途中,突然响起吓人的尖啸,我赶紧跳入旁边的沟渠,躲避袭来的炮火。我当时以为是苏联人发射的喀秋莎火箭弹,但很快明白过来,是我方的多管火箭炮正以燃烧弹覆盖敌军防线。一发发火箭弹从空中呼啸掠过,身后拖着浓浓的烟雾,在夜空映衬下格外显眼。眼前的壮观景象深具破坏性,但也很有吸引力。一发发火箭弹准确地在敌军主战线上炸开,形成一堵巨大的火墙,明亮的火焰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一刻,地壳似乎裂开了,仿佛要把所有生命拖入炽热的熔岩核心。很难想象对面还有什么人能活下来。但苏联人继续对我方阵地施加压力,可能部分归功于他们广阔的领土,另外,他们的兵力几乎取之不尽。
1月中旬,师里几名军官来到我们这处小小的阵地,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敌人的情况。没过多久,上级下令组织侦察巡逻队,探明苏联人的阵地。敌人显然前调了新锐预备队。侦察行动昼间实施,因为能见度较好,但足以说明我们对这项任务深感不安。此处的地形太平坦,顺利完成任务的机会很小。二级下士带队,每当我们犹豫,或是深入骨髓的恐惧阻止我们前进时,他就打出手势,鼓励我们跟上。
苏联人很快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枪声刚刚响起,备受尊敬的班长就挨了致命一枪。我们以猛烈的火力还击,带着阵亡战友的遗体返回己方阵地,没再遭受更多伤亡。我对班长没太多了解,但这位南施蒂里亚人突然阵亡,对全班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他以体贴周到的做事方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短时间内就把全班打造成训练有素的战斗分队。更重要的是,他教会我们如何在东线生存。
师里的军官可能觉察到敌人正在酝酿某种行动,天黑后不久就离开我们的阵地。一队士兵赶来,把二级下士的遗体带回卡缅卡,跟其他阵亡者一同下葬。地面冻得很深,必须用集中装药炸开才能挖掘墓穴,这些炸药也用于战斗。第二天晚上,一名年轻的候补军官带着口粮到来。他刚刚开始前线见习,立即接掌了我们这个只有5名士兵的班。日子还得过下去。
1944年1月,气温没再下降,但冰冷的东风刮过第聂伯河低地,甚至比以前更凛冽,我们班的掩体冻彻寒骨。掩体里倒是有个小炉子,可燃料总是不够。卡缅卡位于我们后方,是个典型的乌克兰穷村子,甚至没标在任何地图上。一座座房屋的木顶早已焚毁。某个晚上,我们在一栋房屋的阁楼上翻寻,想给取暖的炉子找点干小麦。阿尔萨斯人摁亮电筒,虽说时间很短,但足以让苏联人发觉,他们立马用大口径机枪开火。我们匆匆离开时,子弹嘶嘶作响地从耳边掠过。我们幸运地找到些柴火,好歹当晚能在掩体里取暖了。
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但前线士兵确实经常为某些琐事冒上性命危险,而这些琐事在平民生活中显得稀松平常。有一次,我想给家里带来的毛衣除虱,毛衣里好多虱子,只要脱掉毛衣,虱子就会爬到掩体的地上。这件毛衣至少有一个月没洗了,于是我把我最暖和的衣服放在仍有余温的暖炉上。此举有点鲁莽,因为我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直到毛衣发出烤煳的焦味才惊醒。可惜毛衣毁了,已经没办法再穿,我只好冻着。阿尔萨斯人开玩笑说,至少我把虱子消灭了。
1944年1月的最后几天,苏联人又一次企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他们投入大批兵力和装备。我和主射手几乎一直在战斗。为确保火力持续不断,也为了准头更好,我们把机枪安在三脚架上。红军士兵高喊着吓人的“乌拉”向前冲来,主射手朝他们猛烈开火,我是副射手,主要任务是瞄准,还要及时换上新弹链。幸亏当时弹药充足,否则我们根本没办法长时间守住这片阵地。红军最后在稍北面取得突破,导致我们再也无法扼守登陆场内的阵地。敌人投入强大的坦克力量,企图包围我们,尽快收复更多领土。他们很快达成了目的。
2月1日,一名传令兵赶到我们班的阵地,不仅送来口粮,还传达了后撤令。我们只带野战背包和弹药,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放在马车上,那些马车此时就等在稍后方。当晚,友邻师几名步兵赶来接防我们的阵地。跟我们不同,他们的装备较差。我们好歹穿着带风帽的冬季防寒外套,还有毡靴,可那些步兵只穿着国防军的长大衣,脚上是钉有平头钉的行军靴,模样看上去很憔悴,我不由得怀疑他们能否长时间守住阵地。
我找到一个看上去宛如来自古代的步兵,把我们存放备用弹药的地方告诉他。他似乎有点听天由命,漠不关心地听取了我介绍的情况,随即缩入暖和的掩体。每次跟军帽上也佩戴雪绒花徽标的战友并肩奋战,我都很自信,可我们现在不得不依靠常规步兵师。更糟糕的是,协同作战的也许是一个个拙劣的战斗群,在这种情况下,灾难往往会迅速降临。我多次注意到国防军各兵种的巨大差异,更别说德国军队与盟友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了。
2月2日凌晨,我们终于离开阵地,赶往后方的尼科波尔。我们的目标是经常光顾的第聂伯河渡场。就好像大自然也联合起来破坏德国军队后撤似的,化冻从一开始就给我们造成大麻烦。除此之外还有雨夹雪,一条条小径很快沦为深不见底的泥沼。
我们在第聂伯河东侧的后撤还算顺利,但在渡场附近遇到混乱的局面。长长的后撤纵队从陡峭的第聂伯河岸堤蜿蜒而下,一路延伸到对岸的内陆,活像一条巨大的蠕虫。数百辆卡车、履带式车辆、马车首尾相连,紧挨着停在原地,等待继续后撤。孤零零几门高射炮仍在阵地内,炮管深具威胁地指向天空。为了让车辆动起来,在场的人倾尽全力,有时候需要动用一整支部队。许多马匹活活累死了,结果挡住身后车辆的去路。
我们这群山地兵的情况要好些,携带的驮畜很健壮,即便面对眼下的状况,还是取得不错的进展。一支战地宪兵巡逻队指示我们去北面,远离这座大型浮桥。于是我们把宽阔的泊位让给其他后撤纵队,找了个狭窄、不适合车辆通行的小码头,顺利渡过第聂伯河。
我们在尼科波尔西北面的第聂伯河西岸占据新阵地,掩护己方部队继续后撤。敌人这次没跟我们接触,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何处,但西面传来的隆隆炮声不是个好兆头。苏联人前进了多远?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先遣部队又在何处?尼科波尔城内一次次响起剧烈的爆炸。我方工兵显然正在炸毁所有重要的军用设施,以免这些东西落入敌人手里。尼科波尔城内腾起熊熊烈焰,从我们的阵地上也能看见。那座城市满目疮痍,上方的夜空呈现出鬼魅的红色,是个坏兆头。
尼科波尔登陆场内留下很多东西,战友、牲畜、军用物资等,对了,还有一个半月前跟我一同到达那里的许多年轻士兵无忧无虑的劲头。
战争把它古老的规则强加给你,你无法怀着世上所有美好的意愿躲避这些规则。当时的选择很有限:要么负伤,要么被俘,要么送命。逃离东线只有这几个办法。但这三个选择都是我急于避免的,至于能拖多久,尽力而为吧。
引言
序幕/一月的某天
第一章/童年和少年时期
第二章/军人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尼科波尔登陆场
第四章/乌克兰的冬天
第五章/从布格河奔向德涅斯特河
第六章/罗马尼亚战线土崩瓦解
第七章/匈牙利境内的厄运
第八章/末日临近
第九章/战败的痛苦
第十章/结束的开始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