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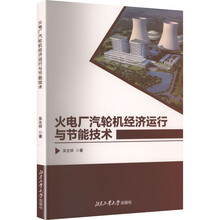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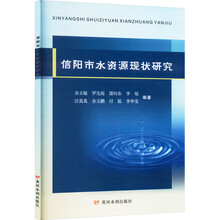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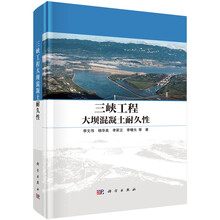




第一章绪论
1.1三峡库区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
1.1.1三峡库区水土流失治理
三峡库区水土流失治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年水利部将湖北省宜昌、秭归、巴东三县列入葛洲坝库区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县。1988年,鉴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及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国务院以国函〔1988〕66号《国务院关于将长江上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的批复》,确定将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及陕南地区、嘉陵江中下游和三峡库区水土流失严重区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实施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工程(简称“长治”工程),其中三峡库区的治理范围涉及湖北、重庆两省市的21个县(市、区),三峡库区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也由此拉开帷幕(廖纯艳,2009)。据统计,“长治”工程在三峡库区治理水土流失的面积为1.88×104km2(赵健等,2015)。2006年《关于划分国家最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将三峡库区列为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2010年《三峡库区水土保持规划》获国家批复,水土保持工作进入新阶段。2013年《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再次确定三峡库区为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随着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库周绿化示范工程等各类生态建设项目的相继实施,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措施体系由坡面整治工程(包括坡改梯、坡面水系、田间道路、坡面植物篱等措施)、沟道工程(包括谷坊、拦沙坝、塘堰整治等措施)、水土保持林草工程(包括水土保持林、经济果木林、种草等措施)、生态修复工程(包括补植、沼气池、围栏、圈舍、封禁治理等措施)及人居环境试点工程(包括垃圾处理、改水改厕、污水处理等措施)五部分组成,其中以坡改梯、坡面水系、水土保持林、经济果木林(以下简称“经果林”)、封禁治理*为常见。
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三峡库区县(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明显缓解,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为3.88×104km2,占三峡库区土地总面积的66.90%。到2000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为2.96×104km2,占三峡库区土地总面积的51.00%,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5.90%。到2010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2.36×104km2,占三峡库区土地总面积40.90%,与20世纪80年代、2000年相比,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减少26.00%、10.10%。到2018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1.92×104km2,占三峡库区土地总面积的33.28%,与20世纪80年代、2000年、2010年相比,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减少33.62%17.72%、7.6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11;廖纯艳,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03)。
1.1.2水土保持效益评估
水土保持效益评估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估可为改善和预防水土流失、保护和改良水土资源、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系统健康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也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优化提供客观标准(李智广等,1998)。
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通过设立径流小区等方式对比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沙效应(潘希等,2020),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水土保持效益评估的国家之一。为评估水土保持工程效益,展现水土保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推动水土保持效益评估标准化,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发布了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规定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包括基础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4个方面,并统一了评价指标与测算方法。后来,众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围绕水土保持效益评估,在指标和方法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王昌高等,2003;王禹生等,1999),极大推动了我国水土保持效益评估工作的发展。随着遥感(remote 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3S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以及我国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和推进,水土保持效益评估也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水土保持效益评估主要特点为:①评价对象更为全面,涉及以防治自然水土流失为目标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和以防治人为水土流失为目标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两大领域(王泽元等,2016);②评价方法不断更新,从依靠定性描述发展为采用数据统计、模型模拟、人工智能等定量评价(徐伟铭等,2016;廖炜等,2014;刘彬彬等,2014;李梦辰,2013;吴高伟等,2008;楼文高,2007;韦杰等,2007)。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在快速提升我国水土保持效益评估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水土保持效益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水土保持效益评估方法方面,国外相关研究较少且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徐伟铭等,2016;陈衍泰等,2004)。研究人员和管理者提出多种方法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评价,其过程主要是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再通过专家咨询法、文献频数法或主成分分析法赋予指标权重,*终运用评价方法完成效益评估。研究方法的探索经历了由简到繁、由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过程,由之前的简单对比和分析项目区治理前后的各项指标数值变化情况,逐渐转向于应用定量评价模型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潘希等,2020)。2008年,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对我国水土保持效益评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目前全国大部分相关评价工作仍以该方法为基础。
在水土保持效益指标方面,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规定了基础效益(15项指标)、经济效益(7项指标)、社会效益(13项指标)和生态效益(8项指标)4类共计43项指标。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为主要构架,国内学者基于评价目的,结合研究区特点、专家选取、以往学者的共识及指标数据可量化和可获取性等,提出各自研究所需的效益评估指标体系(赵建民等,2012;尹辉等,2010;姚文波等,2009)。国外学者对水土保持效益指标有不同的研究视角:Lambert等(2007)选用水土保持投入及产出相关的经济效益指标对水土保持效益进行了评价;Carter等(2009)通过对不同植被状态的耕地生物多样性、植物寄生生物密度、容积密度及C、N含量的测定来评价水土保持效益;Hernandez等(2005)通过测定K、P、C、N等元素在不同试验区的含量情况,分析了橄榄园在土壤贫瘠的沙质土壤上的水土保持效益;Pimentel等(1995)认为很多方法可以用来估算水土保持带来的效益,比如直接测算工程的实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具体价值,还可以测算人们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支付意愿等;Trimble(1999)分析了土壤侵蚀和河流泥沙输移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使用的评价方法是基于水文观测数据和河流断面测量数据等构建的一套适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涵盖坡面侵蚀、河道冲淤等方面。
总体而言,水土保持效益可以通过多方面多项指标来反映,但在实际效益评估时不可能应有尽有、面面俱到,对其涉及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价,只能按照工程治理的目的等主要因素筛选出与评价目的相关度较高的部分典型指标。因此人们在进行水土保持效益评估时,常把评价区域内部所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水土保持活动作为整体的变量,水土保持活动对整体可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应结合评价的目的及区域特点等因素,从中筛选出与评价目的相关度较高的部分典型指标,构建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比选合适的评价模型,对评价区域进行总体评价(王国振,2020)。
水土保持保土减沙效益评估主要侧重于评估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对土壤资源原位截留、减少土壤运移流失的效益,评估方法主要有三种(张平仓等,2017):第一种是布设不同条件下的径流小区,对水土流失进行观测统计,以此推算类似下垫面条件地块的减沙保土量,其优点是可以直观反映水土保持效益,主要应用于坡面尺度,但缺点是由于实际下垫面条件千差万别,设置径流小区缺项难免,区域或小流域地块划分及对照计算难以实现,而且也需要专门修建观测设施;第二种是布设水文卡口站,通过观测某区域或小流域出口处径流泥沙,统计分析间隔一段时期后某区域或小流域水土保持保土减沙效益,其优点是可以整体反映某区域或小流域情况,但缺点是需要专门布设监测设施,目前大多数小流域都难以实现,而且监测结果难以反映某区域或小流域的局部特征和贡献;第三种是模型模拟,将区域或小流域划分为若干网格,采用某种模型分别计算每个网格土壤流失量,直观反映局部的水土流失特征,再通过计算,统计分析区域或小流域土壤流失量,加上时间维度,即可计算水土保持保土减沙效益,该方法优点是无需布设相关硬件设施,也可以反映整体和局部效益贡献,但缺点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模型,因此模型成为该方法的关键。目前对于区域或小流域尺度水土保持保土减沙效益评估,大多采用的是模型模拟法,根据建模时是否考虑侵蚀机理过程,可将众多土壤侵蚀模型分为两大类,即经验模型与物理模型。经验模型是通过长期野外观测的资料,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土壤侵蚀因子与侵蚀量进行拟合,最终得出土壤侵蚀模型;物理模型则是通过分析土壤侵蚀的机理过程,建立侵蚀因子与土壤侵蚀过程之间的物理关系,并以此建立土壤侵蚀模型(蔡强国等,2003;符素华等,2002;郑粉莉等,2001)。与物理模型相比,经验模型形式简单且所需数据容易获取,因此在全世界广泛应用。土壤侵蚀定量评价与预测主要利用经验模型,较为常用的经验模型有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USLE)(Wischmeier et al.,1965)、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RUSLE)(Renard et al.,1997)及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hinese soil lossequation,CSLE)(刘宝元等,2010)。
1.1.3水土保持提质增效
水土流失与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破坏、水环境污染三大水问题密切相关,解决三大水问题必须要搞好水土保持(张金慧等,2019)。我国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的基本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广大农村居民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依靠土地生存发展,一些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急需补齐治理短板,提升治理速度和质量,提供更多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大江大河上中游、东北黑土区、西南岩溶区、南水北调水源区、三峡库区等为水土流失重点区域,通过政策机制创新,加快推进坡耕地综合整治、侵蚀沟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和贫困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山青、水净、村美、民富为目标,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试点,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中央重大战略中的作用(蒲朝勇,2019)。“十四五”时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提高水土保持率为目标,以推进水土流失减量降级与提质增效并重为主线,以健全制度和强化落实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强化人为水土流失监管,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着力提升监测支撑能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支撑。特别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考虑水土流失状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老百姓需求,尊重规律,科学确定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