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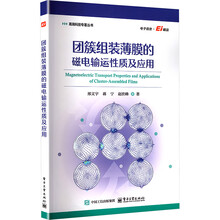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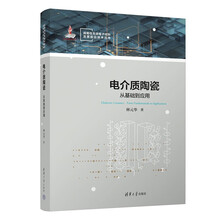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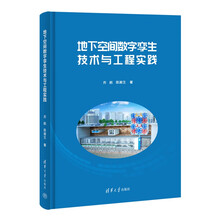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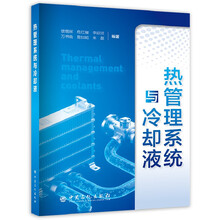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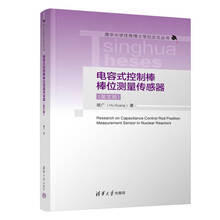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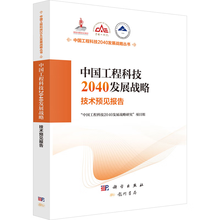
第1章 绪论
1.1 飞机雷击背景
雷电是自然界雷暴云中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释放其内部电能的强电磁脉冲现象,在极短时间内传导强大电流、极高温度和强电磁场,同时伴随强光、雷鸣等物理现象[1]。雷击现象频繁出现在云层内部、云际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也会发生于雷暴云与建筑物或飞行器之间,具有温度高、时间短、大电流、高电压和强电磁辐射等放电特性。雷雨云中正、负电荷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分离而出现两个不同极性的电荷区域,当雷暴云中电荷密集处的电场达到25~30kV/m时出现先导放电。放电通道中的空气粒子受高温和电场作用发生热电离,同时在电场作用下发生电离而转化为热等离子,随着大气电场逐渐增强而发生梯级先导,在电子雪崩的驱使下先导逐渐向下发展,与其诱发的迎面先导汇合形成热等离子体放电通道。雷击主放电阶段持续时间极短,一般在50~100μs;包括余辉阶段在内,一段完整的雷击放电过程一般存在高电流冲击、连续低电流作用和高电流脉冲分量反复冲击等过程,持续时间在0.03~1s之间。放电主通道常表现为无规则的弯*状,如图1-1所示,除主通道外还伴随许多条分叉小通道,雷电附着后会出现一次或多次的回击现象。此外,雷雨云中可能存在多个电荷中心,一次放电结束后会引起其他电荷中心继续放电,从而出现许多条连续的放电通道,如图1-2所示。
图1-1 雷击放电通道
图1-2 连续多条放电通道[1]
雷击的损坏能力极强,潜在危险性较高,释放的物理效能可造成建筑损坏、森林火灾、油库失火、能源损耗、电子故障等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雷击灾害已经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建筑和电力部门逐渐扩展到航空、航天和通信等领域,影响空间运载火箭、地面飞机和航空器等的正常飞行[2]。一般威胁飞机飞行安全的自然灾害有暴雨天气、低能见度、严重颠簸、风切变、表面结冰和雷击等,其中雷击是昀为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对飞机造成的破坏包括机身电弧附着点处金属熔化出现孔洞以及雷达罩和天线的破坏等[3],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维修记录显示对飞机雷击损伤的维修数量约占总维修数量的17%[4]。
飞机遭遇雷击主要有途经强电场区域自我触发的先导放电和拦截自然雷电而形成的双向先导放电两种情形,通常一架固定航路的飞机,平均每年要遭到一次雷击[5]。据统计飞机遭遇雷击主要由自身触发放电造成,飞行高度在7km以上,飞机遭遇雷击都是由其自身触发放电引起,飞行高度在7km以下只有10%的情况由飞机拦截造成[6]。据资料记载,飞机平均航行1000~1500小时就遭受一次雷击[7],尽管飞机飞行会极力避免在恶劣天气下飞行,但从近几十年报道的飞机事故来看,由雷击造成飞机事故的损失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飞机雷击事件如图1-3所示。随着现代先进飞机的发展,为提高飞机飞行性能,采用更先进的综合航空电子系统和更轻便的复合材料,这些复合材料和灵敏的电子系统在遭遇雷击后反而更容易被破坏。
图1-3 飞机雷击事故
针对飞机在雷电环境中的飞行安全问题,飞机设计手册关于飞机防雷击设计有着严格的规定。我国对飞行器雷击问题研究起步较晚,雷击防护系统大部分参考国外的设计标准,航空器的雷击问题已成为我国现代航空器设计的重大技术瓶颈之一[8]。在现代航空业,无论军用飞机还是民航客机都不可避免在雷雨天执行飞行任务,特别是全天候作战飞机,都面临雷击问题,过去飞机主要采用金属材料制成,即便遭受雷击也能很快地将雷电流传导到翼尖和尾翼的放电刷上,通过放电刷把雷电流释放到空气中,金属良好的导电性保证了金属材质的飞机很少因雷电造成严重损坏。但出于降低成本和减重的考虑,现代先进航空器结构上采用非金属材料越来越多,特别是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虽然碳纤维是良好的电导体,但环氧树脂的电导率却很低,故碳纤维复合材料整体表现为电导性差[9]。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电阻率是铝的2000倍,雷击后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损伤,主要有表面的热烧蚀和冲击开裂,因此现代飞机设计中明确要求复合材料结构在机翼、机头雷达罩和油箱中应用时需要考虑防雷击问题。
目前,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飞机结构材料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铝合金、钛合金和合金钢等传统金属材料已经难以满足飞机结构的设计需求。此外,为了降低飞机的机身重量,提高飞机的续航能力,复合材料因其具有轻质、可设计性强、比强度大、比模量高等一系列优点,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飞机结构设计上。如波音公司自B737开始就已经在飞机结构设计中采用复合材料,而在新一代的大型民航客机B787上复合材料的使用量占到飞机结构总重量的一半左右,A350客机中复合材料的使用量同样达到了飞机结构总重量的52%。我国自主研发的支线客机ARJ21和大型客机C919在其中央翼盒和机身尾段均采用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但复合材料是由导电性较好的碳纤维和电绝缘的环氧树脂组成,与传统的工程材料相比复合材料整体导电性能较差,从而导致复合材料结构电磁屏蔽性能的缺失,使得飞机结构对雷电效应非常敏感,在飞行的过程中遭遇雷击的概率也大大增加,雷击造成的后果也更为严重[10]。
雷电流对飞机结构造成的损伤类型可分为直接效应损伤和间接效应损伤。直接效应损伤主要是由雷电流在复合材料结构内部传导造成的损伤,其损伤形式包括复合材料的灼烧、熔融、相变、分层、等离子体的热力冲击、汽化反冲和结构畸变等[11],此种损伤形式对飞机机身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带来巨大危害。间接效应损伤主要是由于雷电流在复合材料内部传导时产生的电磁场和电势差对电子、电气设备、电网或电网终端造成的损伤,这些损伤主要是由于复合材料内部传导大电流而导致磁场发生变化,可使电子、电器系统的瞬间电压发生变化,影响电子控制和使显示系统失灵[12],此种损伤形式对飞机航电系统和控制系统带来巨大危害。
随着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各地的航线、航班数量大幅度增加,关于飞机遭受雷击事件的报道也频繁出现。据统计,由于雷击导致的飞机事故每年都在百起以上,迄今为止已超过2500架飞机被雷电击毁,严重影响飞机飞行安全。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飞机雷击事故主要有: 2000年,一架运七客机在武汉下降过程中遭受雷击坠毁;2004年,一架南非小型飞机在长沙附近遭受雷击坠毁于湘江;2005年,一架麦道DC9客机在尼日利亚降落时,因雷击坠毁造成多人死亡;2006年,一架波音客机在武汉机场降落过程中起落架舱内发现雷电附着;2007年,沈阳飞机维修基地的一架B6205飞机的升降舵后缘、发动机喷口和左侧机身等部位发现多处雷击痕迹;2010年,一架B737客机在哥伦比亚圣安德烈斯岛降落过程中遭遇雷击而实施紧急迫降,飞机坠毁并断为三截,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2015年,一架B757飞机在冰岛*都机场起飞后便遭受雷击,机头被雷电击穿;2016年,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的一架B777-300ER型客机,在穿越雷暴区时右侧机翼被雷电击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2017年,一架新西兰客机在被闪电击中后被迫返回奥克兰;2018年,英国哈里王子乘坐的私人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途中被雷电击中,幸运的是飞机没有失事;2019年,一架苏霍伊超级喷气机100客机遭遇雷击后电气自动化设备失灵,被迫返航后实施硬着陆,致使机身断裂起火,事故导致41人遇难。据估计大约每一架民航飞机每年至少遭遇一次雷击,在雷暴环境中飞机本身触发的雷电可能会导致飞机外部结构和航电系统的损坏。迄今为止至少已有2500架飞机遭受雷击毁伤,我国的民用和军用飞机都曾发生过多起因遭遇雷击而坠毁的事故[13]。雷击对飞机正常航行的威胁已不容忽视,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1.2 飞机雷击研究现状
1.2.1 雷电观测和放电机制
雷电放电现象本质是大气火花放电,经科学家们对雷电放电现象的深入研究,并随着雷电测量技术和试验水平的日益提高,对雷电形成机制和活动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目前,针对雷雨云起电机制和雷击放电通道形成机理,国内外一般借助雷电观测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雷雨云主要由大气对流运动而形成,解释雷雨云起电现象的理论有很多,比如对流起电、粒子碰撞起电、温差起电、大雨滴破碎起电和粒子感应起电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雷雨云的起电过程,但实际起电机制非常复杂,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多种起电机制的综合作用,目前尚未形成一种雷击起电机制可用于解释所有雷雨云起电现象,通常需要结合多种起电机制分析雷雨云中不同极性电荷区域的形成机理[14,15]。
为了研究放电通道的先导起始机理、梯阶先导发展特性、分叉特征、连接过程、通道内电磁场变化和温度分布规律等,常借助于高速摄像、光谱探测、声呐测量及电磁辐射探测等技术手段完成。基于时间分辨照片和测量数据,分析雷击放电机理和变化规律。通过对大量云对地放电现象观测结果的分析,Berger等[16]依据测量得到的雷电流波形特征,将云对地放电划分为正极性放电和负极性放电两类。据Rakov等[17]调查发现,在全球雷电活动中云对地放电案例占1/4,其中90%属于云对地负极放电,10%属于云对地正极放电。雷电梯级先导形成过程利用普通高速摄像装置难以分辨,鉴于负极放电梯级先导与实验室长间隙放电现象相似,Gorin等[18]研究了6m长间隙负极放电的梯级先导过程,梯级初始脉冲电晕为一系列丝状通道分支,随后逐渐演化形成负极流注。Gallimberti等[19]结合长间隙放电试验结果,归纳总结了雷击放电过程及其基本原理,当初始电晕周围空间电场强度达到一定阈值时,流注前端受到电子雪崩的推动而逐渐向下发展形成一条负极下行先导放电通道,与地面附近激发出的正极上行先导相连,形成一条完整的放电通道,发生附着后由附着点沿原通道返回并中和负极先导中的负电荷,完成*次回击过程,雷击过程一般存在多次连续回击现象。Warner等[20]在美国一座高163m的塔上测量到了两次自然雷电在*次回击前的通道连接过程,计算出两次上行连接先导的二维长度都大于200m,上行先导的二维平均速度在104~ 105m/s之间变化,下行先导的二维平均速度在105m/s量级。
在雷电光学观测方面,因雷电通道内的峰值温度高达上万度,各气体粒子受激发出现光辐射,雷电等离子通道温度、空间分布结构和内部物理特征等可以借助多普勒展宽、分子带状光谱和谱线相对强度等光谱分析途径获得[21]。王杰等[22,23]利用无狭缝光栅摄谱仪进行了自然雷电的光谱观测试验,结合等离子体传输理论计算出通道内温度、压强、粒子数分布和平均电离度等特征,放电通道的温度通常在27000~30000K以上。董彩霞等[24,25]利用无狭缝高速摄谱仪观测雷电回击过程,通过分析雷电时间分辨光谱结构,依据谱线波长和相对强度等信息分析了通道内温度、热导率和扩散系数随时间的变化特征。此外,使用高时间分辨率的特殊高速摄影可对雷电放电的演变方向和分叉特性进行实时记录,但是单个观测站点只能得到雷电通道的二维图像。Liu等[26]利用两个不同角度的摄像机来拍摄雷电通道,利用图形化重建方法将三维重建算法简化为一系列的二维几何问题,延长每个图像上的垂直法线,如果不同图像上的两条法线相交则建立一个单位像素高的圆柱体,昀后将一系列圆柱体堆放在一起得到三维放电通道。在雷电声学探测方面,章涵等[27]利用麦克风阵列采集雷声信号,设计了一套由麦克风列阵和便携式数据采集存储设备组成的单站雷电通道三维定位系统,利用声学方法可以对雷电进行三维定位,但不能准确测定雷电通道的三维特征。在雷电电磁学测量方面,通常借助雷电甚高频(Very High Frequency,VHF)电磁脉冲辐射源定位技术确定雷电产生的电磁特性和放电发展路径,可以认识雷雨云中的放电过程和雷暴电荷结构特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