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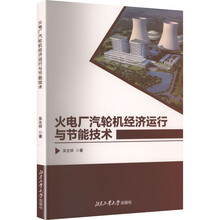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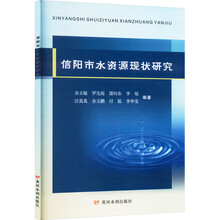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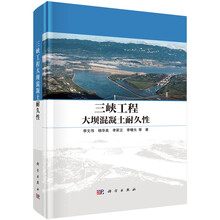




第1章绪论
珠江三角洲是国家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区位。其三江汇流,八口入海,河网交错,地形地貌和水动力条件十分复杂,堪称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河口之一。珠江口属于珠江流域的泄洪、纳潮区,直接关系着流域防洪安全、水资源综合利用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全局性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水资源的安全、高效利用和水环境的保护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前提。
1.1珠江三角洲概况与珠江河口河网治理研究意义
1.1.1珠江三角洲概况
珠江位于我国南部[图1.1(a)],多年平均入海径流量达3.36×1011m3[1-2](马口站、三水站和博罗站径流量总和),仅次于长江,为我国第二大河;珠江全长2320km,次于长江和黄河,为我国第三长河,流经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自治区)及越南的东北部。
珠江流域水系发达,主要由西江、北江和东江组成,控制流域面积4.54×105km2。如图1.1(b)所示,西江上游分南盘江、红水河两段,中游分黔江、浔江两段,全长2075km,西江控制77.8%的珠江流域面积,控制流域面积3.531×105km2;北江长468km,控制流域面积4.67×104km2,占整个珠江流域面积的10.3%;东江长520km,控制流域面积2.70×104km2,占整个珠江流域面积的5.9%[3-4]。三大河流在下游广东中南部交汇沟通,共同冲积形成珠江三角洲[图1.1(c)]。珠江三角洲位于112.50°E~114.25°E,21.75°N~23.50°N,东西跨越近150km,南北纵深约200km,集水面积超过2.68×104km2,占珠江流域面积的5.9%。珠江三角洲内河道纵横,交错沟通,形成了复杂的河网系统;珠江三角洲内的水流通过八大口门注入南海,其中东四口门自东向西分别为虎门、蕉门、洪奇门和横门;西四口门自西向东分别为崖门、虎跳门、鸡啼门、磨刀门[5]。
1.水系特点
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三角洲系统之一,其主要包含两大区域,即上游径流为主的河网区及下游潮流为主的河口(湾)区[6]。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上起西江、北江思贤滘和东江石龙;下至八大口门潮位站——大虎站(虎门)、南沙站(蕉门)、万顷沙站(洪奇门)、横门站(横门)、灯笼山站(磨刀门)、黄金站(鸡啼门)、西炮台站(虎跳门)和官冲站(崖门)[图1.1(c)];主要由沟通互连的西北江河网、相对独立的东江河网及注入珠江三角洲的诸小河(潭江、流溪河、增江、沙河、高明河、深圳河等)组成,河网面积达9750km2,河网密度为0.68~1.07km/km2[2,7]。西江与北江在佛山三水的思贤滘汇合,来水来沙重新组合分配后经马口站、三水站注入下游的西北江河网;西北江河网拥有近百条水道,全长超过1600km,集雨面积达8370km2,占珠江三角洲河网区总面积的86%;而径流最小的东江流经东莞石龙站后直接注入下游相对独立的东江河网,其与西北江河网隔狮子洋相望,主要有5条水道,总长约138km,集雨面积为1380km2,占河网区总面积的14%[8]。
珠江三角洲河口(湾)区前缘东起九龙半岛九龙城,西到赤溪半岛鹅头颈,包含八大入海口门及其延伸区,水域面积达6536km2,海岸线曲折迂回,延伸522.4km,离岸岛屿众多。其中,东四口门的来水来沙均注入珠江三角洲东侧的喇叭形河口湾——伶仃洋;西四口门中的虎跳门和崖门则与三角洲西侧的喇叭形河口湾——黄茅海连通;磨刀门直接注入南海,鸡啼门注入三灶岛与高栏岛之间的水域[4,9]。因此,整个珠江三角洲呈现出“三江汇流、河网交织、径潮叠加、八口入海”的水系格局。
2.气候水文特征
1)气候特征
珠江流域地处北纬21°~27°,位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多年平均日照时间为1282~2243h,多年平均气温在14~22℃,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2200mm,多年平均蒸发量在900~1600mm[10]。受季风的影响,珠江流域的气候特征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从时间上看,有明显的干、湿季,全年80%的降水集中在湿季(4~9月),干季(10月~次年3月)降水仅占全年的20%[11]。从空间上看,气温、降水与蒸发均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渐增加的趋势,西北部多年平均降水量和蒸发量仅为400~800mm与900~1200mm,东南部河网多年平均降水量和蒸发量则在1600mm与1200mm以上[10,12]。
2)径流泥沙特征
珠江三角洲径流丰沛,但时空分配明显不均匀。如表1.1所示,西江控制的流域面积最广,西江高要站多年(1957~2020年)平均流量为6932m3/s,注入三角洲的径流达2.186×1011m3/a,占三角洲总径流的77%;北江控制的流域面积次之,北江石角站多年(1954~2020年)平均流量为1325m3/s,注入三角洲的径流达4.178×1010m3/a,占三角洲总径流的15%;东江控制的流域面积最小,东江博罗站多年(1954~2020年)平均流量为731m3/s,注入三角洲的径流达2.32×1010m3/a,占三角洲总径流的8%[12]。
受季风气候干湿两季降雨控制,珠江三角洲径流存在明显的年内变化,洪枯季节差异显著。与降雨湿季相对应,每年4~9月为径流洪季,高要站、石角站、博罗站径流分别占年总径流量的77%、85%和72%左右;对应降雨干季,每年10月~次年3月为径流枯季,高要站、石角站、博罗站径流分别占年总径流量的23%、15%和28%左右。此外,受全球气候年际变化的影响,流域内降雨有丰枯年之分,三角洲径流同样存在年际差异,最小年径流量于1963年出现,最大与最小年径流量之比可达2.6~9.8。
珠江是典型的少沙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约为0.3kg/m3。泥沙通量中悬移质占主导地位,推移质仅为悬移质总量的10%~15%[13]。由于径流量较大,珠江多年平均输沙量可达8.87×107t,经珠江三角洲河网入海的沙量每年约为7.24×107t[14]。受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影响,珠江三角洲河网泥沙通量也有显著的季节差异。西江高要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为6.45×107t,占珠江三角洲总输沙量的89%;北江石角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为5.5×106t,占珠江三角洲总输沙量的8%;东江博罗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为2.4×106t,占珠江三角洲总输沙量的3%[15]。输沙量年内洪枯季分配也不均匀,洪季河流含沙量高,使得输沙量过度集中,西江高要站洪季输沙量占全年输沙量的94.6%;北江石角站洪季输沙量占比更高,为95.4%;东江博罗站则为89.3%;三站相应的枯季输沙量占比很少,仅为4.6%~10.7%[9]。
3)潮流潮汐特征
珠江三角洲河网是典型的感潮河流,受到径流与潮汐的共同作用,在洪季河网内的水动力由径流主导,枯季水动力则转由潮汐主导。河网内的潮汐过程由进入南海的太平洋潮波经珠江河口湾水域从八大口门传入[16]。珠江河口及河网内的潮汐类型为不正规半日混合潮,每个太阴日内有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但涨、落潮时及涨、落潮差分别不等;一年中春分与秋分前后潮位分别达到最高点与最低点,并且潮差较大,到夏至和冬至潮差较小,一般冬潮小于夏潮[17]。
受到天文、地形、水文等条件的制约,珠江河口平均潮差在0.86~1.63m(表1.2),属于弱潮河口。口门的潮差呈现出由中部向两侧递增的趋势,中部的磨刀门和鸡啼门潮差较小,最东侧的虎门潮差为八大口门之首,其原因是伶仃洋河口喇叭形的收敛形态对潮汐能量具有辐聚作用,使得潮波在河口湾内传播至湾顶虎门的过程中振幅不断增大[18]。在多年平均径潮比(多年平均净泄量与涨潮量之比)方面,磨刀门平均径潮比高达5.53,远大于1,是典型的河优型河口;两侧的虎门和崖门平均径潮比分别为0.25与0.30,远小于1,是典型的潮优型河口。总体上看,东四口门的潮汐动力要强于西四口门,八大口门中以虎门的潮汐动力最强。
外海潮波从八大口门进入河网内部后,在径流与河床底部摩擦等作用下逐渐衰减,能量逐渐耗散,使得潮差呈现出由下游向上游递减的分布态势。如表1.3所示,河网顶端马口站与三水站的最大潮差和平均潮差分别在0.6m、0.34m左右,若考虑八大口门潮差均值,潮汐由口门传播至河网顶端,衰减幅度超过70%。总体而言,北江河网内部站点的潮差普遍要大于西江河网内部站点的潮差,这与东四口门的潮汐动力要强于西四口门有关。此外,河网两侧站点的潮差也要明显大于河网中部站点的潮差,这是由两侧口门虎门和崖门的潮差较大导致的。
受径流洪枯季节分配不均匀的影响,三角洲地区潮流界、潮区界处于不断变动状态。表1.4给出了珠江三角洲主要支流在洪枯季节的潮流界和潮区界。如表1.4所示,洪季降雨丰沛,受大量径流下泄压制,潮区界位于河网中部,距下游口门40~55km,而潮流对河网水动力的影响十分微弱,潮流界均在距口门10km以内的下游范围,有的甚至被强烈的径流推移至口门外,如洪奇门、蕉门;三角洲顶部河网的潮汐影响十分轻微甚至消失,但口门附近仍受潮汐控制,对整个河网区总体而言,洪水期是径强潮弱。枯季降雨不足,河网径流锐减,潮动力明显增强,整个河网处于感潮状态,潮区界甚至可以上溯至梧州—德庆段,距磨刀门300km,潮流界相较于洪季也明显上移至距口门60~160km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