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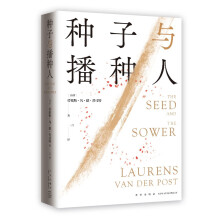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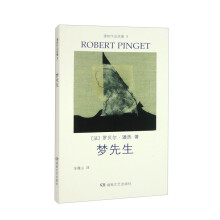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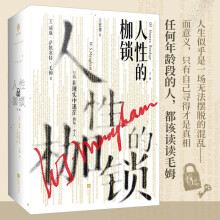






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爱情杰作,一部很地道、更好读的大师经典入门
轻巧体量×浓郁风味,打开“马尔克斯宇宙”的命运钥匙!
在这里同时读到《百年孤独》的魔幻,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迷狂
献给浸在爱之泪水中的人们:爱情能战胜一切?没错,可你蕞好别信。
“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是名为魔鬼的爱情,还是名为爱情的魔鬼?致幻想象力,极尽魔幻,又极尽绚烂
爱是人类历史中蕞重要的话题,一切都与爱有关。年龄使我认识到,情感和柔情,发生在心里的那种东西,终归是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
怪诞,恐怖,闪闪发光,阴郁。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世界。——《纽约时报》书评
内封设计+模切书签赠品,精致华丽、心动典藏
奴隶们的院子里吵吵嚷嚷,人们正在那儿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祝生日,在老侯爵的年代,这里曾是一座城中之城。到了他的继承人这一代,在贝尔纳达在马阿特斯榨糖厂用一只左手便可以掌控奴隶和面粉这两宗不正当生意的年代,它也还大体保持了原样,而现在,这一切的辉煌都成了过去。贝尔纳达因为贪得无度已经在走向死亡,这院子也缩小成了两间用棕榈叶铺顶的木板棚,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余晖已消失殆尽。
在如此喧闹的音乐之中,自家的和其他富贵人家的奴隶欢聚在一起,这样的歌舞场面不可能沉闷。女孩玩得很尽兴,她的舞跳得比非洲人还要欢快潇洒,又能改变嗓音用好几种非洲语言唱歌,模仿鸟鸣和动物的叫声时搞得鸟儿和动物都有点不知所措。
按照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去世前的吩咐,最年轻的几个女奴用烟灰给女孩涂黑了脸,往她受过洗礼的肩上套上了一串又一串萨泰里阿教项链,又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头长发从来没有剪过,要不是每天把辫子盘成好多圈,连走起路来都要碍事。
在两股相反力量相融合的影响之下,她一点一点长大了。她身上像妈妈的地方极少。相反,她瘦削的身材、无可救药的腼腆、白皙的皮肤、沉郁的蓝眼睛,以及那一头亮闪闪的纯铜色头发,都来自父亲。她一举一动都静悄悄的,无影无形。她的妈妈被她这种奇特的天性吓住了,在她的手腕上挂了串小铃铛,为的是在昏暗的家里能随时知道她在哪儿。
生日过去两天后,女佣无意间把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了贝尔纳达。贝尔纳达一边用香皂洗当天第六次热水澡准备上床睡觉,一边回想此事,等走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了:猎狗们无缘无故地一直狂吠到天亮,她有点担心它们是不是得了狂犬病。于是,她拿起烛台来到院子里的木棚中,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躺在油棕榈吊床上睡得正香,那吊床还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留给她的。女佣没告诉她咬在了什么地方,她撩起女孩的袍子,用灯照着,顺着那条麻烦的辫子一点一点地查看女孩的身体,那辫子缠绕在女孩的身上,活像条狮子尾巴。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被咬的地方:伤口在左脚踝上,已经结痂,另外,脚后跟上还有几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擦伤。
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狂犬病例既不少有,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最臭名昭著的要追溯到某个小贩,他平日里经常带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那猴子的行为举止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这只动物在英国人海上围城期间得了狂犬病,往主人脸上咬了一口,逃进附近山里去了。那个倒霉的小贩后来在一次恐怖的发病中被人们乱棒打死,直到多年以后,母亲们还把这事编成街巷小曲,用来吓唬孩子。小贩死后不到两个礼拜,一群恶魔般的野猕猴白日里从山上下来,祸害完猪圈和鸡栏,又闯进了教堂。它们号叫着,嘴上沾满了带血的泡沫,当时人们正在那里为庆祝英国军队战败高唱感恩诗。然而,这些最恐怖的场面并没有被载入历史,因为它们发生在黑人群体当中,而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野外围出场地,给被咬者施以从非洲传来的魔法,算是治疗。
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教训,在那些一经出现便无可挽回的症状出现之前,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谁都不会往狂犬病上面去想,也不会想到其他潜伏期长的疾病。贝尔纳达·卡布雷拉也是一样,她想,奴隶们编起故事来总是比基督徒更快更离奇,而哪怕仅仅一个简单的狗咬人事件都可能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她对自己的推断十分自信,就没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也没再想着。直到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女佣独自一人去了趟市场,看见巴旦杏树上挂了条死狗,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条狗是得狂犬病死的。女佣一眼便认出了狗脑门上的白斑,还有那一身的灰毛,正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狗。但是贝尔纳达听说之后还是不以为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伤口早已经结痂,那几处擦伤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