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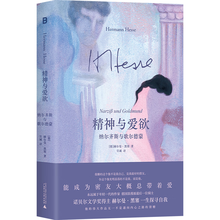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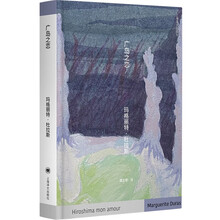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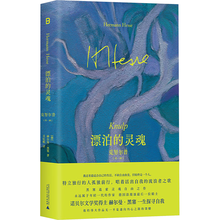





1
飞机飞行在城市上空,预示灾祸的飞鸟。发动机的噪声是雷声,是冰雹,是风暴。风暴、冰雹和雷声,日日夜夜,着陆起飞,对死亡的重复演练,一种空洞的喧嚣,一次震颤,一段废墟里的回忆。飞机的弹药舱仍旧空着。观察飞鸟的占卜官笑而不语。没有人抬头看天。
2
石油从大地的静脉中涌出,原油,水母的血液,恐龙的脂肪,鳄鱼的鳞甲,蕨类森林的浓绿,巨型木贼,沉陷的自然,人类之前的时代,被掩埋的遗产。由侏儒看守着,他们吝啬、精通魔法、生性恶劣。传说,童话,魔鬼的宝藏得见天日,为人所用。报纸上说些什么?石油之战,争端尖锐化,人民的意志,把原油还给人民,石油短缺的舰队,针对输油管的袭击,军队守卫钻井架,沙阿完婚,围绕孔雀宝座的阴谋,隐身幕后的俄国人,波斯湾的航空母舰。石油令飞机往来不息,让新闻界无暇喘息,石油带给人恐惧,用不算太猛烈的爆炸驱动着送报人的轻便摩托。报贩们伸出冻僵的手,摸到油墨未干的报纸,闷闷不乐,骂骂咧咧,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被雨浇得浑身湿透,啤酒让脑袋变沉,烟草浸透了神经,睡眠不足,噩梦未散,皮肤上留着情人或伴侣的气息,肩膀上的刺痛,膝盖上的风湿。这个春天很冷。那些新鲜事也毫无暖意。紧张关系,争端冲突,仿佛生活在应力场中,东部世界,西部世界,又好像生活在拼缝处,或者是断裂带。时间多么宝贵,战场上喘息的间隙,都来不及好好透口气,备战又开始了,备战让生活变得昂贵,使快乐受到限制,到处都藏着火药,足够把这个星球炸上天。新墨西哥的核试验,乌拉尔山的核工厂,他们在仓促修补过的大桥废墟里钻出爆破室,他们讨论着建造又准备着拆除,他们任由已经出现裂痕的东西继续分崩离析:德国分裂成了两块。报纸散发出运转过热的机器的气味,从中还能闻出噩耗,闻出惨烈的死亡、错误的判断、如同儿戏的破产,闻出谎言、锁链和污秽。层层报纸粘在一起,油墨晕开了,连通篇的恐惧都被浸透。新闻标题在大喊大叫:艾森豪威尔视察驻德美军,要求德国做出防务贡献,阿登纳反对中立化,协商陷入僵局,难民怨声载道,数百万人被强迫劳动,德国巨大的步兵潜力。养活各种画刊的是飞行员和军官们的回忆,是那些坚定不移的随波逐流者的忏悔,是各种人的回忆录,勇敢的,正直的,无辜的,被震惊了的,被耍弄了的。越过镶着橡树叶和铁十字的衣领,他们从报刊亭的墙面上投来愤怒的目光。是在推销报纸上的广告版面吗?还是在征召一支军队?而空中轰鸣着的飞机,属于另外一些人。
3
演员的更衣室里,大公正在生产制造中。这里一块奖章,那里一条缎带,一枚十字章,一枚耀眼的星章,命运的穗绳,权力的项链,闪光的肩章,银色的饰带,金色的羊毛,金羊毛勋章,金羊毛,燧石上的羔羊皮,为赞颂和荣耀救世主、童贞马利亚、圣安德烈而设,为保卫和发扬基督的信仰与神圣的教会而设,为宣扬美德和散播良俗而设。亚历山大开始出汗。恶心折磨着他。白铁皮、圣诞树彩灯、刺绣制服衣领,所有东西都紧箍着他,让他动弹不得。服装师俯在他脚边来回摆弄,为他戴上马刺。在大公那双擦得锃亮的长靴面前,服装师算什么?就是一只蚂蚁,一只尘埃中的蚂蚁。更衣室里亮着电灯,在这个与亚历山大身份不相称的木板隔间里,灯光与黎明的曙色开始了缠斗。又是这样一个早晨!亚历山大的脸在脂粉下白得像奶酪,整副面孔如同一块凝结了的牛奶。烧酒、葡萄酒、不充足的睡眠在亚历山大的血液里发酵、咆哮,不断从内部敲击着他的颅骨。天还没亮他就被带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强壮的女人还躺在床上,梅萨利纳,他的妻子,欲望战马—这是她在夜店里赢得的美称。亚历山大深爱他的女人。考虑到这份爱,这桩婚事就还称得上美好。熟睡的梅萨利纳面容浮肿,睫毛膏已经晕开,眼皮看起来仿佛挨过拳头,毛孔粗大的皮肤与日晒雨淋的马车夫无异,这得归功于酒精的功效。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性格啊!亚历山大便是在这样的性格面前俯首称臣的。他跪倒在床边,向沉睡着的戈耳工俯下身去,亲吻她歪斜的嘴,吸入她呼出的酒气,仿佛吸进了从她唇缝中逸出的一缕经过蒸馏提纯的魂灵。“怎么?你要走了吗?放开我!啊,我不舒服!”这就是她在他面前的模样。往浴室走的时候,他的脚踩到了玻璃碴。沙发上睡着阿尔弗雷多,一个女画家,身形矮小,头发蓬乱,全然不省人事,倒也不失可爱,疲乏和失望在脸上交织,紧闭的双眼被皱纹环绕,一副引人同情的模样。在清醒的时候,阿尔弗雷多是一个有趣的人,一支毫不吝惜自己光亮的火把—她机敏过人,或讥讽揶揄,或娓娓道来,时而轻声细语,时而又一针见血,语惊四座。这是唯一一个还让人笑得出来的人了。墨西哥人是怎么称呼女同性恋来着的?听起来像“玉米饼”,托提莱拉,大约是一块烘干的扁平蛋糕片。亚历山大没有想起这个字眼。太可惜了!他应该借来用用。浴室里站着另一个女孩,他一时兴起从大街上带回来的,他凭借自己的名望引诱了她,凭借这副家喻户晓的歪斜嘴脸。电影海报的标题:亚历山大饰演大公,德国制造的超级电影,大公和渔女的故事。她被他网住,被他打捞上来,又被他撤下餐桌。她叫什么来着?苏珊!沐浴中的苏撒拿。她已经穿上了衣服,批量生产的廉价连衣裙,丝袜上抽丝的地方抹了肥皂,身上搽了他妻子的娇兰香水,闷闷不乐,满腹牢骚。事后她们向来是这副样子的。“怎么样?感觉好吗?”他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其实他有些尴尬。“混蛋!”每次都是这样。她们都想要他。亚历山大,伟大的情人!知足吧!他得去冲个澡了。楼下的汽车疯狂地鸣笛。他们还得指望他。观众是冲着谁来的?是他。亚历山大,大公情事。人们已经受够了,受够了这个时代,受够了遍地的废墟—他们不想再面对自己的忧虑、自己的恐惧、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不愿照镜子般地看到自己的苦难。亚历山大褪下了睡袍。女孩苏珊看着他满身的松垮疲弱,眼神里混杂着好奇、失望和愤怒。他心想:“好好看吧,想说什么就说吧,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我是他们的偶像。”他的鼻腔和喉咙呼噜呼噜地出着气。喷头冲出的冰冷水柱就像鞭子一样打在他松弛的皮肤上。楼下的汽车又在摁喇叭了。他们迫不及待了,他们渴求着他们的大公。房间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叫声,希勒贡达,亚历山大的小女儿。那个孩子在喊:“埃米!”她是在呼救吗?她的声音里透露着恐惧、绝望和孤单。亚历山大想:“我得去管管她,我得抽出点时间,她看起来脸色苍白。”他喊道:“希勒,你已经起来了吗?”为什么她这么早就起来了呢?他对着毛巾喷出鼻息,把这个问题一起喷了出去,然后由着它在毛巾上窒息而死。孩子的喊叫声听不见了,或许是被楼下那些汽车愤怒的鸣笛声盖过了。亚历山大踏进了摄影棚。他已经穿戴整齐,脚上蹬着长靴,靴上佩着马刺。他站在摄像机前。所有的聚光灯一齐点亮。各种奖章在上千烛光的灯光照射中熠熠生辉。这位大众偶像摆好了功架。他们把大公搬上银幕,成为一场超级德国制造。
4
钟声催促着人们去做晨祷。可曾听小钟叮当响?泰迪熊竖起了耳朵,玩具娃娃竖起了耳朵,站在红色轮子上的羊毛大象也竖起了耳朵,连同彩色墙纸上的白雪公主和公牛费迪南,全都听见了那悲伤的歌声。那是埃米,照看孩子的保姆,她拖长声调,好似哭灵一般地唱着,同时用粗糙的刷子擦洗着小女孩瘦弱的身体。希勒贡达在心里默念:“埃米你把我弄疼了,埃米你划到我了,埃米你扯到我的头发了,埃米你的指甲锉戳到我了。”但是面对这个粗壮的乡下妇女,面对这张牢牢凝固着农民特有的朴素虔敬的宽脸,她不敢说出口:她被弄疼了,她正在承受痛苦。这个保姆的歌声—可曾听小钟叮当响?—俨然一种不绝于耳的劝诫,它说:不要抱怨,不要发问,不要欢喜,不要欢笑,不要玩耍,不要调笑,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落入死亡之手。希勒贡达多希望自己还在睡觉。她多希望自己还在做梦,多希望自己正在和玩具娃娃玩耍,但是埃米说过:“当上帝召唤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玩耍呢?”希勒贡达的父母都是坏人。这也是埃米说的。谁都得为自己父母的罪过忏悔。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他们走去教堂。一辆有轨电车急刹在一只小狗面前。狗毛乱糟糟的,脖子上也没有项圈,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保姆在希勒贡达的小手上按了一下,不是友好的、施以援助的揉按,而是一个看守强硬而用力的一抓。希勒贡达望向那条没有主人的小狗。她宁愿追着这只狗奔跑,也不要跟保姆一起去教堂。希勒贡达并紧膝盖,对埃米的恐惧,对教堂的恐惧,对上帝的恐惧,拽扯着她幼小的心脏—她往下沉,她向后缩,眼前通向教堂的路就被拉长了。但是女看守的手钳着她不放。时间还很早。天还很冷。这么早希勒贡达就踏上了去见上帝的路。教堂的大门都是厚实的木板,沉甸甸的木料,铁配件,铜螺栓。上帝也会害怕吗?还是说上帝也被关在里面了?保姆握住了精心锻造的门把手,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恰好容人钻进去见上帝。靠近上帝的地方散发着仿佛圣诞节烟花的气味。奇迹已经准备好了吗?早已被预言了的骇人的奇迹,对罪孽的宽恕,对父母的赦免?“这孩子的父亲是个演戏的。”保姆心里这样想着。她的薄唇没有血色,农民的脸上长了一抹禁欲主义的嘴唇,仿佛一道锐利的意欲不朽的笔画。“埃米我害怕。”孩子心想,“埃米教堂这么大,埃米墙要塌了,埃米我不喜欢你了,埃米亲爱的埃米,埃米我恨你!”保姆把圣水洒在瑟瑟发抖的小孩身上。一个男人从大门的缝隙里挤了进来。他顶着一张过街老鼠的面孔,身后是五十年的操劳、工作和忧虑,还有两场战争。两颗泛黄的牙齿在他持续嚅动的嘴唇后面腐烂着,他陷在一场永不停歇的对话里,他在同自己对话—除了他自己还有谁会听他说话呢?希勒贡达踮着脚跟在保姆身后。立柱幽暗惨淡,墙壁布满伤口一般的裂纹。女孩感觉到了吹在身上的冷风,好像是从坟墓里涌出来的寒气。“埃米不要丢下我,埃米希勒贡达害怕,好埃米,坏埃米,亲爱的埃米!”女孩不断恳求她。“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上帝会惩罚她的,自父及子,直到第三代第四代。”保姆在心里默念。信徒跪倒在地。从高处往下看,他们就像是一群忧虑憔悴、惴惴不安的老鼠。神父诵念弥撒经文。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铃敲响了。主宽恕我们。神父感到冷。元素的化体!教会和它的仆人被赋予了力量。炼金术士的徒劳幻梦。空想家和骗子。学者。发明家。实验室,在英国,在美国,在俄国。毁灭。爱因斯坦。窥探上帝的厨房。哥廷根的智者们。被拍摄的原子—成亿倍地放大。自身的清醒与冷静令神父感到苦恼。正在祈祷的老鼠们的窃窃私语像沙粒一样落在他身上。坟墓的沙粒,不是圣墓的沙粒,沙漠里的沙粒,荒漠里的弥撒,荒漠里的布道。圣母马利亚请为我们祈祷。那群老鼠在胸口画了十字。
5
菲利普离开了宾馆,他在那儿过了夜,但是几乎没有睡着。羔羊宾馆,在老城的一条巷子里。他清醒地躺在僵硬的床垫上,出门在外的生意人的床铺,用于交配的无花的草场。菲利普彻底把自己交给了绝望,交给了一桩罪行。命运把他逼进了窄巷。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的翅膀挟着风雨敲击着窗户。宾馆是一栋新建筑,装修新得像刚出厂一样—上过漆的木料,洁净,卫生,寒酸,节俭。一道窗帘,印满了包豪斯墙纸图案,只是太短了,太窄了,太薄了,不足以把大街上的噪声和光亮挡在外头。
透进房间的光亮规律地闪烁着,那是广告牌的灯光,对面的埃卡泰俱乐部正在招揽客人—一片三叶草缓缓展开它的叶子,把菲利普笼罩在其中,随即又消失了。窗台下有输了钱的赌徒在咒骂。醉醺醺的人摇摇晃晃地走出啤酒坊,他们对着墙根撒尿,嘴里唱着“步兵步兵”,卸了任的、受了挫的征服者。楼梯上不断传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这家宾馆是魔鬼的蜂箱,这个地狱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中了无法入睡的诅咒,在每一道单薄的墙壁后面,叫喊,打嗝,把污物冲掉。过了一会儿,月亮穿透了云层,温柔的卢娜,尸身僵直。
老板问他:“您还继续住吗?”他语气粗鲁,冰冷的双眼不信任地打量着菲利普,尖刻的眼神嵌在滑溜油腻的胖脸里,那脂肪里渗着餍足了的食欲、平息了的焦渴、在婚床上发酸了的色欲。昨天晚上,菲利普几乎两手空空地走进这家宾馆。外面在下雨,他的雨伞是湿的,除了一把伞,他什么也没带。他还会再住下去吗?他真的不知道。他说:“是啊,是啊。”“我会付两个晚上的房费。”他接着说。冰冷尖刻的眼睛放过了他。“您就住在这儿的富克斯大街啊。”老板说,他看过了他的登记表。“这干他什么事?”菲利普心想,“他只要拿到钱,这些事和他又有什么关系?”他回答:“我的房子在粉刷。”这是一个可笑的借口,谁都能听出来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会觉得我在隐瞒什么,他会去琢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会猜我在躲什么人。”
雨已经不下了。菲利普走出啤酒坊小巷来到制桶匠广场。他在啤酒坊的入口前放慢了脚步,这段闭锁了的食道,在晨光里散发着呕吐物的气味。广场的另一端是嘉美咖啡馆,美国黑人士兵的俱乐部。巨大的平面玻璃背后的窗帘被拉到了一边,座椅都架在了桌子上,两个女人把前夜里的垃圾冲刷到马路上。两个老头在清扫广场,他们的扫帚扬起了啤酒杯垫子、彩色纸带、酒鬼的小丑帽、揉皱的香烟盒、破裂的橡皮球。这是一股污秽的洪流,老头的扫帚每挥动一下,它就向菲利普逼近一步。夜晚的气息和灰尘,腐败了的、死去了的声色犬马的残渣,最终把菲利普团团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