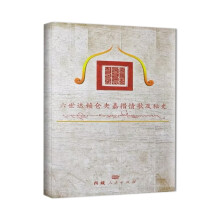一
著名的西洋画大师入江新之助于八年前去世,而他的遗族,无论哪一位都有些奇怪之处。不,其实不能说他们奇怪,或许那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倒是我们这种一般家庭出身的人与之相比更显奇怪。总之,入江家的氛围似乎与寻常人家稍有不同。很久之前,我从这个家的气氛中获得启迪,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我不是畅销作家,作品无法立即于杂志上刊载,长久以来,那部小说被我收在抽屉深处。此前我另外写过三四篇从未发表的压箱底之作,前年早春时,出版社将它们结集成单行本,一口气全部出版。那是一部技巧拙劣的作品集,收录的却是我至今依然喜爱的旧作,是我怀着某种天真、不含任何野心地沉浸在愉悦的心境中创作的。我认为所有“力作”,总显得呆板刻意,日后作者重读,也会产生厌恶感,而格调轻快的短篇不存在这种问题。然而,这部单行本一如既往不太畅销,可我没有特别遗憾,甚至为销量不佳感到庆幸。我很喜欢里面的作品,虽说它们写得不算上乘,完全经不起读者冷静严苛的鉴赏,即是说,净是些不上台面的散漫之作。不过,作者自身的喜爱之情是另一回事。我有时会悄悄把这部天真的作品集摊开在书桌上,一个人品读。这部小说集中,写得最单薄也最为我喜爱的故事,即是我开头提及的以入江新之助氏的遗族为灵感构思的短篇小说。虽说它单薄而孩子气,不知为何,我始终念念于心。
入江家有五位兄弟姐妹,人人喜欢浪漫的爱情故事。 长男二十九岁,法学学士。与人相处时,态度稍显妄自尊大,这是他为了掩饰自身怯懦而刻意戴上的凶恶面具,其实他是非常软弱温柔的人。和弟弟妹妹们去看电影时,他一边嚷着“这部电影拍得不好,愚蠢至极”,一边为电影里武士的义理人情所感,几人中第一个对着屏幕流下眼泪的也总是这位长兄。不错,这简直毋庸置疑。走出电影院,他却会忽然摆出目中无人的不悦神情,一言不发。他曾毫不犹豫地宣称,出生以来,自己从未撒过谎。且不论这番宣言有几分可信,他的确具备刚正纯洁的一面。在学校念书时,他成绩不太好,毕业后也没找工作,坚持待在家里守护家人。最近他研究易卜生,再次读过《玩偶之家》后,有了重大发现,非常兴奋。娜拉恋爱了,喜欢阮克医生。他发现的就是这个。他叫来弟弟妹妹们,指出这一点,并且大声阐释,费力说明,却是白费力气,因为弟弟妹妹们全都纳闷地歪着头,不置可否地笑了,面上丝毫不见兴奋。其实,弟弟妹妹们根本不把长兄放在眼里。他们瞧不起他。
长女二十六岁,尚未出嫁,在铁道省工作,法语非常不错。身高五尺三寸,格外纤瘦,曾被弟弟妹妹们戏谑为“马”。她头发剪得短,戴着圆框眼镜。心胸开阔,很容易与人立刻建立友谊,一心一意地付出,然后被抛弃。这种“付出”是她的兴趣。她很喜欢通过付出与被抛弃,悄悄享受忧愁和寂寥。不过有一回,她对同一科室的年轻男同事着迷,而后一如既往地遭到抛弃,唯有那段时间,她心力交瘁。同对方在办公室打照面又觉得尴尬,她便谎称肺部有问题,在家躺了一周。后来她在脖子上裹了纱布,一个劲咳嗽,就诊时拍了X光片,做了一番精密的检查,医生夸赞她肺脏强健,世间少有。她的文学鉴赏力很高,古今东西的作品无不涉猎。阅读之余,自己也悄悄试着写过一些,把它们藏在书箱右侧的抽屉里。这些日渐积累的作品上方,规规矩矩地搁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于我逝世两年后发表”。有时,“两年后”会被改为“十年后”或“两个月后”,有时甚至被改为“百年后”。
次男二十四岁,是个俗物。就读于帝大医学部,可他很少去上课,身体羸弱,是个不折不扣的病人。他有一副令人惊异的漂亮容颜,但生性吝啬。有一回,长兄被别人欺骗,花了五十日元买下据说是法国散文家蒙田使用过的平淡无奇的旧球拍,回家后得意扬扬地吹嘘,他竟暗自愤怒导致高烧不退。这场高烧,让他的肾脏出了点毛病。他蔑视所有人。当别人发表意见时,无论说什么,他都会发出极度不悦的笑声,犹如鸦天狗一般,他只崇拜歌德,这绝非出自敬服歌德素朴的诗歌格调,似乎是由于他倾心歌德的高层官位。他是个奇怪的家伙。不过,与兄弟姐妹比赛即兴作诗时,他总是遥遥领先,实力不凡。虽说是俗物,但他十分懂得对热情本身进行某种客观的把控。倘若他有心,或许能成为二流作家。此外,家里腿脚不便的十七岁女佣,死心塌地地痴迷着他。
次女二十一岁,是个自恋狂。某家报社征选“Miss日本”时,她打算毛遂自荐,为此历经三天三夜的煎熬挣扎。她想四处呐喊,抒发激动之情,结果在三夜的挣扎思考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因此彻底死心。在兄弟姐妹之中,数她身材特别娇小,只有四尺七寸。不过她模样不错,还算漂亮。她常在深夜裸身对着镜子露出可爱的微笑,也会用HECHIMA COLOGNE清洗白皙丰腴的双腿,俯身亲吻脚趾,陶醉地闭上眼睛。有一回,她鼻尖长出宛如被针尖刺过的小痘子,便忧郁得计划自杀。她有固定的阅读偏好,常去旧书店找明治初年出版的《佳人奇遇》或《经国美谈》一类的书,回家后一面翻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