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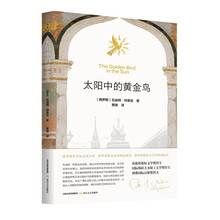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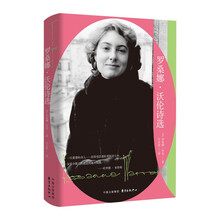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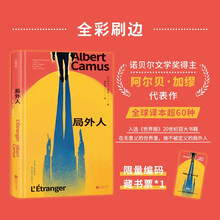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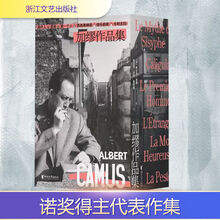


◎ 编辑推荐
※天才艺术家、超现实主义最后的幸存者、2022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主推人物莉奥诺拉·卡林顿疯癫回忆录,简体中文版首度引进!
她曾是戏梦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圈宠儿,路易斯·布努埃尔、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都为之着迷;
在超现实主义成为历史以后,她被公认为为这一运动最后的幸存者;
她的绘画作品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出325万美元的天价;
2022年,她被选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主推艺术家,再次让世人领略其风采;
莉奥诺拉·卡林顿珍贵回忆录——简体中文版首度引进!
※五天心碎的自我剖白,带着冷笑的深渊回望
“《在深渊》毫不留情地记述了精神失常的经历。”
1943年,“二战”撕裂了欧洲,也击溃了莉奥诺拉·卡林顿的生活,
丈夫被捕,纳粹横行,战火延烧……
在失序的世界中,卡林顿走向了疯癫,被关押入院。
逃出疗养院40年后,她用一贯的超现实主义风格,重述了当年的诡谲历程。
※耗尽早熟的青春,谱写女性出逃的颂歌,在疯癫之中找寻生命的真相
“我没有时间当谁的缪斯……我忙着反抗我的家人,并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
成为名媛的律令——来自父亲的巨大压力,要她成为一名跻身上流的淑女;
艺术家丈夫的凝视——被马克斯·恩斯特当作“女囡”,仅仅成为艺术的客体;
战争与暴力的入侵——纳粹、佛朗哥的警察、疗养院的护士,都用身体上的强力逼她屈服;
疯癫是症状,亦是通道。在疗养院之后,她终于抵达新大陆,成为自己。
※跨越三块大陆,历经四十余年,书写、口述、翻译后终成经典人生回望录
1942年,在纽约以英语写成,原稿遗失于前往墨西哥途中;
1943年,在墨西哥用法语给友人口述那段至暗经历;
1944年,译成英语后刊于超现实主义杂志《VVV》上;
1946年,法语口述稿由Editions Fontaine出版社在法国出版;
1987年,卡林顿在法语口述稿和英译本基础上亲自校阅、修订,终得定稿!
※知名设计师汐和操刀,精装小开本典雅便携
知名青年设计师汐和倾情设计,爽朗绿包边书脊搭配素净壳面,呈现灵动与优雅交锋的装帧视觉;
110*185精装小开本,出游、通勤绝佳伴侣。
正是在三年前,我被关进莫拉雷斯医生位于西班牙桑坦德的疗养院里,此前,马德里的帕尔多医生和英国领事宣称我精神失常且无法治愈。偶遇了你——我认为于众人中头脑最清醒的你——之后,我开始在一周前收集带领我穿越知识之初始边界的线索。我必须重新回顾那段经历,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可以让自己受用于你,正如我相信你也会在穿越边境的旅程中帮助到我,助我保持清醒,助我任意戴上、摘取那替我抵御奉从主义敌意的面具。
在话题转向本人经历中的真实事件之前,我想说,社会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对我下的判决,或许、甚至毋庸置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那时的我尚未知晓健康的重要性,我指的是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以此在头脑解放的过程中避开灾难的绝对必要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必要性,即他人和我在一起,我们便可以用自身的知识哺育对方,继而组成整体。我在那个年代没有充分意识到你的哲理,更谈不上理解。我理解的时刻尚未到来。我将在此以最为忠实的方式竭力表达的,彼时仅仅是知识的胚芽。
因此,我会从马克斯被扛着步枪的宪兵第二次押送至集中营的时刻(1940年5月)开始讲起。当时,我住在圣马丹-达代什。我在山下的村庄里哭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再次上山回到我的房子,在整整二十四小时里,通过喝橙花水强制自己呕吐,呕吐间隙短暂地睡了一会儿。我希望那阵阵痉挛或可抑制哀愁,它们如地震般撕扯着我的胃。我现在明白了,这只是呕吐所代表的诸多方面中的一例:我察觉出社会的不公,我希望首先将自身净化,之后再越过其袒露无遗的无能。我的胃是社会的座席,然而也是我与大地上所有的元素联结的地方。它是大地之镜,它所映照的如人物镜像般真实。为了恰切、清晰、忠实地映照大地,必须将厚厚的、层叠的污垢(公认的常规)从镜中——也就是我的胃中——清除;我所说的“大地”,指的当然是天地间所有的地球、星星与太阳,以及微生物星系中所有的星星、太阳与地球。
整整三周,我都吃得极少,小心翼翼地避开肉食,喝下葡萄酒和烈酒,靠土豆和沙拉维生,每天大约吃两个土豆。印象中我睡眠很好。我照料我的葡萄藤,力气大到让农民们感到吃惊。圣约翰节近在眼前,葡萄藤开始吐花,需要经常喷洒硫黄。我也照料土豆,出汗越多我越欣喜,因为这说明我正经历着净化的过程。我晒日光浴,那段日子里,我的体能如此之好,此前或此后都无法企及。
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各种事件:比利时沦陷,德国人进入法国。我对这些事件几乎毫不关心,心中没有丝毫恐惧。村子里满是比利时人,一些士兵闯进我家里,指控我是间谍,威胁要将我就地枪决,因为之前我家附近有人在夜里提着灯笼寻找蜗牛。他们的威胁对我来说几乎毫无威慑力,因为我知道自己命不该绝。
在我独处三周之后,我的多年老友凯瑟琳(她是个英国女人)和一个名叫米切尔·卢卡斯的匈牙利男人结伴从巴黎出逃,并抵达我的住处。一周过去了,我觉得他们并未发现我有任何异常。然而有一天,曾长期接受心理医生治疗的凯瑟琳说服了我,她说我的态度暴露出某种想要再次摆脱父亲的无意识欲望:这里的“父亲”指的是马克斯,一个我若希望存活就必须除掉的人。她恳求我停止折磨自己,另找一个情人。当她说我在折磨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她想错了。我觉得她并没有完整地理解我,这样还不如彻底放弃理解。不过,她的做法倒是帮我恢复了性欲。我疯狂地试图引诱两个年轻男子,但事与愿违。他们丝毫不愿意接受我。而我只能继续伤心地过着禁欲生活。
德国人在快速逼近;凯瑟琳恫吓我,请求我和她一起离开,还说如果我拒绝这么做,她也会留下来。我接受了。我之所以接受,首先是因为在我自身的演变过程中,西班牙之于我如同一次发现。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期望能在马德里为马克斯的护照弄到签证。我感到自己仍与马克斯紧紧相连。这份附着他照片的证件已化为实体,如同我随身携带的是马克斯本人。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凯瑟琳的据理力争多少触动了我,她的话持续不断地在我心中凝结为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惧。对凯瑟琳来说,德国人等同于强奸犯。我并不惧怕被强奸,丝毫不在乎。我内心涌起的惊慌,源于他们如机器人般的存在,一种头脑空空、无血无肉的生命体。
导读
在深渊
后记
文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