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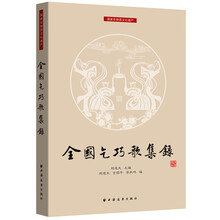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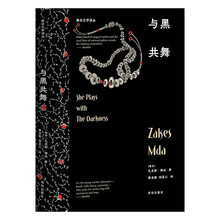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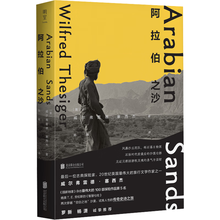


我在暧昧的日本(节选)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即便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更是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刚刚结束的大战的废墟中背负创伤却仍对新生抱持希望的作家们,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美诸国间深深的沟壑。而在亚洲,他们则为日本军队的非人道行为感到痛苦并为之赎罪,进而在此基础上谦卑地祈求和解。他们表现出的这种姿势应长存于人们的记忆,我志愿站在末尾并行至今日。
后现代的日本,无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二义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太平洋战争便是现代化本身带来的扭曲后果。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已从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重新出发。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是新日本人最基本的道德观。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却并非清白无辜,作为曾践踏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侵略历史的污垢。而且,广岛和长崎那些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武攻击的死者们、那些罹患放射病的幸存者及其第二代(不仅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许多人),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
目前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参与联合国的军事任务、协助恢复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不积极。听到这些批评,我们十分心痛。然而,日本为了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是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之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对于西欧而言,这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因为西欧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对于遵循良心而拒绝服兵役者,人们抱持着宽容的态度。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一直存在,试图利用国际上所谓外来压力尝试发起的策动,也包括在这些策动之中),无疑将是对亚洲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呢?身为小说家,我无法不如此想象。
曾支撑了旧宪法的市民情感将绝对价值置于远超于民主主义原理的更高处,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民主主义宪法下,这种情感不只是一种怀旧,更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存续着。假如与这种情感相连接,日本人再度将另一种有别于战后重新出发之道德观的原理予以制度化,那么,我们在业已崩溃的现代化废墟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所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功了。生而为人,我不得不如此想象。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为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胚芽——使得日本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像慢性病般孕育出的暖昧(ambiguity)急剧发展,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怪:如同战后忍受着赤贫,却并未丧失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隐忍着对前途的强烈不安。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的繁荣,被统合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逐渐增强的潜在势力之中,目前正不断呈现出新的样态。
“大江健三郎文集”编委会名单
代总序
目录
正文
大江健三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