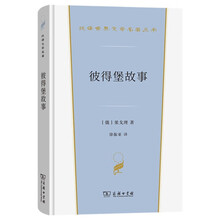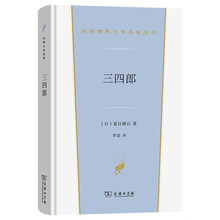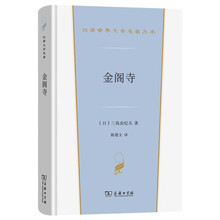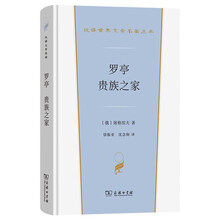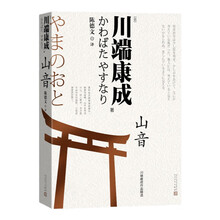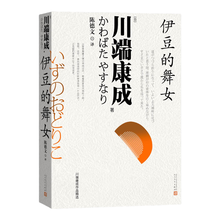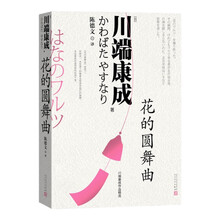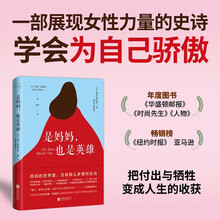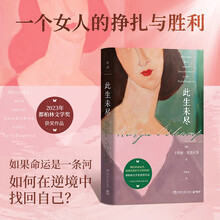《“自我”迷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小说与民族性建构》:
如果说当初的“爱有等差”让他为了“亲密的朋友”而不惜牺牲对政治身份的忠诚,同是“爱有等差”也让他最终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阿皮亚在论述“有根的世界主义”时,曾区别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与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关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一致的是,阿皮亚同样关注到了“民族”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主观任意性因素,即将一个民族中的个体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参与的故事”,民族对个人的伦理意义“与足球和歌剧有意义的原因是相同的:它们都是自主的行为者关心的事物”。阿皮亚同时指出,相对而言,“国家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它们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人民在乎它,而是因为它们通过需要得到道德证明的强制方式来管理我们的生活”。简单来说,“民族”概念更强调个人的自主行动力,而“国家”概念则更突出对个人的强制约束力。在2010年出版的《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一书中,阿皮亚进一步阐释道,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一种对国家成就的骄傲情绪,“你至少要高度赞赏国家的某些成就,否则很难对国家产生信任之感”。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从一开始,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不如民族与个人的关系那么“主观而亲近”,一旦国家的强制职权被滥用,个人对国家的认同便会随之遭受打击,相比而言,个人对民族的忠诚绝不仅仅是由出生地决定的,因此,对民族的情感偏私性也会更加强烈。
需要指出的是,阿皮亚区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有等差”,并非为民族中心主义提供伦理合法性,而是一如既往地强调世界主义伦理实践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有根的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对朋友、家庭、民族还有国家的情感偏私之所以具有伦理意义,是因为它们不仅关注了自我对他人的道德义务,更关注了个人(包括自我和他人)作为一个真实具体的生命主体的自主权利。回到《同情者》的主人公,他“爱有等差”中的“爱”针对的并非政治信仰、国家意识形态,也并非抽象的人性以及所谓的“正义和善”等普世价值,而是身边真真切切存在、有血有肉的人。他鞭笞美国对越南战争死难者的无视,也同样讽刺越南政府对民众疾苦的漠然;他斥责美国的道貌岸然,也同样揭露北越的表里不一,因为它们都没有把“人”当作人看。正是出于他对实实在在的“人”的爱,他会忍不住同情拥有“敌人”身份的南越士兵和流亡的难民,他会在犀利地指出“光复大军”天真痴梦的同时,敬畏他们“重获的男子气概”,甚至在写给北越上司的信中称他们为“英雄和梦想家”,因为他们想得到的是“国家(哪怕已不复存在)的承认和铭记”。正是出于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他会在失去对北越的身份认同后,和波一起再次踏上从西贡逃亡的难民之路,因为他此时誓死捍卫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要活下去”。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家,他成了以“个体生命”为终极关怀的世界主义的阐释者。
此外,小说主人公也实现了罗蒂所言的“自由主义者”与“反讽主义者”的统一。按照罗蒂的阐释,“自由主义者”强调对普遍人性、普世价值坚定的信念,致力于实现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自由”,而“反讽主义者”强调对终极语汇持续的质疑,追求个体不断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这两个在理论上看似无法调和的理念在实践中则有可能完美结合,即罗蒂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他们质疑普遍主义,反对“(自我和他人)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的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和机缘的基础”,但他们同时相信人类团结的可能,因为“这些无基础的欲望之中,包含了一个愿望,亦即希望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在罗蒂看来,将人与人集合为一体的不是形而上学家坚持的世界“真理”,而是自我与他人的通感,因此,“团结不是反省所发现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对其他不熟悉的人所承受痛苦和侮辱的详细原委,能够提升感应相通的敏感度,那么,我们便可以创造出团结”。团结的意义不仅在于将自我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的过程,不仅描述了陌生人,也重新描述了我们自己,由此,个体的完美与全人类的和谐成为相互兼顾的有机体。在《同情者》中,出于对包含了你、我、他个体苦难的“感同身受”,主人公将“爱有等差”的关怀“推己及人”,可谓真正实现了超越固有社群界限的“团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