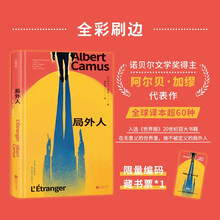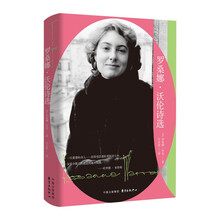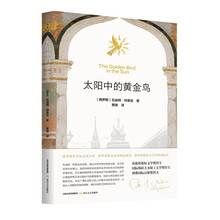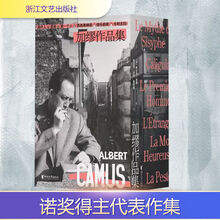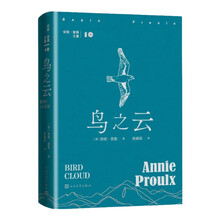信吾在去年花甲之年,吐了一点儿血,可能是从肺里咯出来的。事后他未做细致的检查,也没有好好疗养,后来倒是并无大碍。
他的身体也没有因此而迅速衰老,毋宁说皮肤反而变得润泽。卧床半个月,眼睛和嘴唇简直像返老还童一般。
信吾以往没有结核症状,六十岁了初次咯血,总觉得有点凄怆,所以有时便拒绝医生的诊察。修一认为这是老顽固,信吾却不以为然。
保子或因身体健康,睡眠很好。信吾却睡眠不佳。他想,兴许是半夜里遭到保子鼾声的影响才醒来的吧。保子十五六岁就有打鼾的毛病,据说其父母为矫正这个毛病煞费苦心。她结婚后虽然不打鼾了,可五十岁以后又复发了。
信吾心情好的时候,会捏住她的鼻子摇晃,她仍不停息,信吾便掐住她的脖颈摇晃。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感觉这长年相伴的肉体又老又丑。
今晚心情不好,信吾打开电灯,盯了一眼保子的脸,便掐住她的脖颈摇晃,把汗都摇出来了。
只有保子停止了鼾声,信吾才感觉触摸的是发妻的身体。念及于此,他的心头掠过莫名的哀伤。
他捡起枕边的杂志。因天气溽热,便起身打开一扇雨窗,蹲在那里。
月夜。
菊子的连衣裙垂挂在雨窗外,是令人生厌的浅白色。信吾凝望着它心想:大概是洗涤后忘记收回了,或是让夜露去除汗渍?
“吱嘎,吱嘎,吱嘎……”
庭院里传来蝉鸣声。那是左侧那棵樱树上的蝉鸣。信吾疑惑,蝉怎么会发出如此可怕的声音?可确实是蝉鸣。
蝉也怕做噩梦吗?
蝉飞进屋里,落在蚊帐的下缘上。
信吾抓住那只蝉,没有蝉鸣。
“哑蝉啊!”
信吾嘀咕了一句。这显然不是那只会叫的蝉。
信吾使劲儿将蝉扔向左侧那棵高高的樱树,免得它看到亮光再飞进来,却无法确定扔到了哪里。
信吾抓住雨窗望向樱树,想确认蝉是否落在了樱树上。月夜幽深,仿佛深邃地延向一侧的远方。
还有十天才到八月,但秋虫聒鸣。
他仿佛听见夜露从一片树叶滴落到另一片树叶上的声音。
信吾蓦然听到了山音。
没有风,接近满月的月亮晶莹透亮。小山被裹挟在夜间潮湿的冷气中,山上的树林轮廓朦胧,并无风中摇曳之感。
信吾所在的檐廊下,羊齿草叶亦纹丝不动。
有时,夜间耳闻镰仓山谷的波涛声。所以,信吾怀疑那是海音,实为山音。
它虽像远方的风声,却有地鸣般深厚的底力。信吾似乎能在脑海里听见这种声音,他以为是耳鸣,摇了摇头。
声音停息。
信吾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他不寒而栗,莫非那是死期将至的预告?
他想冷静地确认到底是风声、涛声,还是耳鸣,统统不对。他听见的确实是山音。
那声音恍若魔鬼鸣山而过。
陡坡笼罩在充满潮气的夜色中,山前仿佛有一堵黑魃魃的高墙。小山堵在信吾家的庭院前,说是高墙,其实就像半切的鸡蛋竖立着一样。
高墙旁边和后面都是小山,山音似乎来自信吾家的后山。
透过山顶林木的间隙,可以望见几颗星星。
信吾在关木板雨窗时,突然想起了一件怪事。
约莫十天前,信吾在新屋的客厅里候客。客人没来,却来了一个艺伎,之后又进来了一两个。
“把领带解下来吧。这么热……”艺伎说。
“嗯。”
信吾听任艺伎解下领带。
两人并不相识。艺伎将领带塞进信吾置于壁龛边上的大衣兜里,然后谈起她的身世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