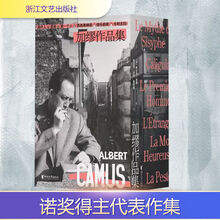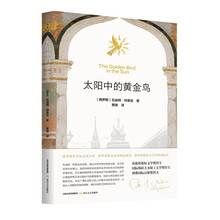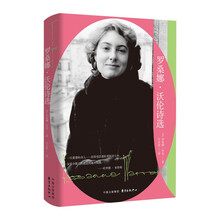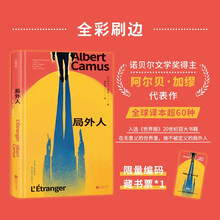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我的安东妮亚》:
我们发现俄国佬彼得正在挖土豆,便高高兴兴地进屋在他的厨灶边暖身子,看他堆在储藏室以备过冬的那些西葫芦和圣诞节吃的瓜。当我们带上铲子骑马离开时,安东妮亚建议我们在犬鼠窝停停,挖开一个洞穴看看。我们可能会弄清那些洞到底是垂直向下,还是像鼹鼠洞一样水平延伸,是否那些洞穴在地下互相连通,是否穴枭在里面筑有用羽毛垫底的窝。我们说不定还能弄到些犬鼠幼崽、穴枭蛋或蛇皮。
那个草原犬鼠聚居地大约铺展了十英亩宽。上面的草已被啃得短乎乎平展展的,所以那片草地不像周围那样蓬茸繁芜,火红一片,而是像一大块灰色的天鹅绒。各洞口之间相距几码,分布得相当规则,仿佛那片聚居地真被划出了一条条街衢似的。人们总会觉得那下面的居住者过着一种有条不紊、和睦融洽的生活。我把花花公子拴在一片洼地下面,然后我们开始四处转悠,想找到一个容易挖开的洞。那些犬鼠像通常一样都在外面,几十只一群地蹲在各自的洞口。当我们走近时,它们摇着尾巴冲我们叫了一阵,随后便都钻到了地下。那些洞口前都有小片小片的沙砾,我们猜想那是从长长的地下甬道中挖出来的。我们在各处还发现一些较大的沙砾堆,它们离任何一个洞口都有几码远。如果是犬鼠在挖掘的过程中将沙砾刨出,它们如何能刨得那么远呢?我就是在这样一片沙砾上遇上了那番险情。
当时我们正在察看一个有两道出入口的大洞。那个洞以平缓的坡度朝地下倾斜,所以我们能看见那两条通道汇合的地方,由于经常使用,通道地面有一层松松的尘土,犹如一条车马频繁的乡间马路。我正弯腰屈膝慢慢后退,忽听安东妮亚一声惊叫。她站在我对面,指着我身后用波希米亚语大声嚷着什么。我猛一转身,发现在一片干燥的沙砾上摊着一条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蛇。在冻了一夜之后,那条蛇当时正在晒太阳,在安东妮亚尖叫之前它肯定一直在睡觉。当我转过身时,它正松弛地拖长身子以波浪形躺在地上,活像字母“W”。它猛地抽动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盘卷起身子。它不仅仅是条大蛇,我觉得——它活像马戏团的一个怪物。它那身可憎的肌肉,它那种可厌的滑动,不知咋的使我直想呕吐。蛇有我的腿那么粗,看样子连磨石的碾压也不可能结束它那令人作呕的生命。它抬起了可怕的小脑袋,尾部的角质环发出嘎嘎声响。我没有逃跑,因为我没有想到逃跑——假如当时我身后是道石墙,我那种无路可逃的感觉也不可能更强烈。我看见它的身子已盘紧——我记起这下它该松开身子蹿起来了。我冲上前去,用我手中的铲子猛砸它的头部,铲刃正好横着砍中了它的脖子,它立刻像一圈粗绳似的瘫在我脚下。这下我便挥铲猛砍以解心头之恨。安东妮亚虽然赤着双脚,也跑上前来站到了我身后。甚至当我已把那颗丑陋的蛇头完全砸扁,它的身子也还在盘卷蠕动,盘到第二圈又松开,跌落回地上。我走到一边,背过身去。我感到像晕船一般难受。安东妮亚跟着我过来,大声问道:“哦,吉姆,它没咬你吧?你肯定?我告诉你时你干吗不跑开呢?”
“谁知道你叽里呱啦嚷些什么?你本可以告诉我有条蛇在我身后!”我使着性子说。
“我知道我让你很不高兴,吉姆,我当时吓坏了。”她从我口袋抽出手帕想替我擦脸,可我从她手中一把将手帕抢了过来。我想当时我脸色很难看,正如我感到很难受一样。
“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勇敢,”她令人欣慰地继续道,“你简直就像大男子汉。你等着它抬起脑袋,然后给它致命的一击。你就一点儿不害怕吗?现在我们把这条蛇带回去,让大家伙儿看看。这地方还没人见过像你打死的这么大的蛇。”
她用这种语调说个不停,直说得我开始觉得我曾渴望有这次机会,并喜出望外地欢迎它的降临。我俩小心翼翼地回到那条蛇跟前;蛇还在盲目地蠕动,其丑陋的腹部翻转朝着阳光。蛇身微微发出一股臭味,并有一线浅绿色的液体从它被砸碎的头部渗出。
“你看,东妮,那就是它的毒液。”我说。
我从衣袋里掏出根长绳打了个活结,当我用绳结套蛇时,东妮用铲子替我抬起了蛇头。我们把它拽直,用我的短柄马鞭量了量;它大约有五英尺半长。它有十二个角质环,但其尾部尚未开始变得尖细就突然断了,所以我坚持认为它以前肯定有过二十四个环。我向安东妮亚解释,这意味着它有二十四岁,它肯定在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儿了,它从野牛和印第安人时代就一直留在这儿。当我翻动它时,我开始为它感到骄傲,对它年岁之老迈和躯体之庞大产生了一种敬意。它似乎就像那条最古老的恶蛇。不可否认,它的同类已在所有热血动物的潜意识中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当我们把它拖进那片洼地的时候,花花公子惊得跳到了缰绳允许它退到的地方,而且浑身直打哆嗦,不让我们靠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