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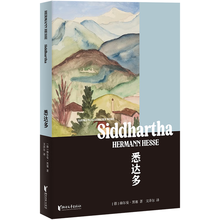









在这部作品中,2021年诺奖得主古尔纳不仅续写漂泊异乡者的孤独与挣扎,完美诠释何谓“回不去的故乡,融不入的他乡”,更是首次聚焦于移民后代所遭遇的身份危机,揭示出种族中心主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伤害,并尝试探讨出路何在。
1、一天
一天,远在麻烦开始之前,他一句话都没有跟人说就悄悄溜走了,从此一去不回。后来,又有一天,在过去了整整四十三年之后,在一座英国小镇上,他刚一迈进自家大门,就倒地不起了。那天出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刚刚下班回到家;可一切本来就已经太晚了。他不管不顾,听之任之太久了,而除了自己,他没有别人可怪。
他早就预感到了要出事,预感到了自己要垮。这不是自打他记事起就徘徊在他身边的那种对毁灭的恐惧,而是另一种预感,仿佛某个处心积虑又肌肉发达的东西不慌不忙地向他压来。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击,更像是一头野兽缓缓地扭头看向他,认出了他,随即伸出肢爪来要将他扼杀。就在虚弱感掏空了他身体的同时,他的思维依旧清晰;清晰如斯的头脑里,冒出的却是荒唐的想法:这一定就是饥寒至死,或是被压在一块巨石下面窒息而死的感受吧。哪怕他此时心急如焚,这样的类比还是让他眉头一皱:瞧见情节剧疲劳的后果如何了吧?
下班的时候他就觉得疲惫,是那种偶尔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莫名其妙找上门来的疲惫,近几年来尤为频繁,每当这时他就只想坐下来,什么也不干,直等到那精疲力竭的感觉消退,或是等到有双强有力的臂膀过来将他抱起,带他回家。如今他老了,至少也是快老了。这样的愿望就像是一段记忆,仿佛他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将他抱起,带他回家。但他认为那并不是记忆。他人越老,心头的愿望有时就越幼稚。他活得越久,他的童年就离他越近,越来越不像是对他人生活的遥远幻想了。
在公交车上,他努力想找出那疲劳感的根源。这么多年了,他还在这么干,努力想把事情搞明白,寻找种种解释,藉此减轻那种恐惧感:生活还会让怎样的事情发生呢?每天结束的时候,他都要回顾一遍自己走过的路,直到他找对了那种种不幸的正确组合——正是这些不幸让他在一天终了时如此虚弱——仿佛这样的认知(如果这算得上认知的话)真能缓解他的痛苦。衰老,首先登场的很可能就是它了,长期损耗,无可替换的磨损件。或者是早上紧赶慢赶着去上班,其实他迟到个几分钟,没有人会在意,也没有人会犯愁,而这样子又急又累地赶一路有时会让他一整天都喘不过气来,烧心地痛。或者是他在员工厨房里给自己泡的那杯有问题的茶,让他的肚子里面汩汩冒泡,预示着腹泻的到来。他们把一罐牛奶放在外面一整天,没盖盖子,就放在那里一面吃灰,一面饱吸他们来来去去时带进来的腐气。他真不该碰那牛奶的,可他抵挡不住啜上一口茶的诱惑。或者,他纯粹就是劳累过度又没掌握技巧,去又推又搬那些他根本就不该碰的东西。又或者,他可能是心痛了吧。他从来都不知道心痛何时会来,从何而来,要待多久。
可就在他坐上公交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身上出了点不同寻常的事情——那是一种越来越强的无助感,让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他身上的血肉一面发热,一面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空虚感。一切发生得慢条斯理:他的呼吸节奏变了,他开始战栗,出汗,眼看着自己垂头弓背,蜷成一团自暴自弃的人类形态,对此他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具等待痛苦、等待解体的人体。他冷眼旁观着自我,他的胸腔、髋关节和脊柱的分解让他有一点惊慌失措,仿佛肉体和精神正在彼此分离。他感觉到膀胱传来一阵剧痛,意识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又慌乱。你在干什么?犯病了吗?别发神经了,深呼吸,深呼吸,他对自己说。
他下了公交车,步入二月的空气中——那是寒流突降的一天,他身体虚弱,浑身发抖,遵照自己的指令做着深呼吸。他没穿够衣服。他身边的其他人都穿着厚重的羊毛外套,戴着手套,围着围巾,仿佛他们凭着实践经验,早就知道这天到底有多冷,而他,尽管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却还是不知道。又或者,不同于他,他们也许听了电视和收音机上的天气预报,然后兴高采烈地拿出了他们专为这样的用场才压在衣橱里面的厚衣物。他身上还穿着那件他一穿就是大半年的外套,足以抵挡雨水和寒意,而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又不至于太热。他从来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不同的场合和季节囤积一橱的衣服鞋子。这是一种勤俭节约的习惯,于他而言已不再必要,可他就是改不了。衣服只要穿着舒服,他就喜欢一直穿,直到穿破为止;他还喜欢想象,假使他能看见自己从远处走来,那他仅凭身上的衣服,就能一眼认出自己来。而在那个寒冷的二月傍晚,他为自己的节俭,或者是抠门,或者是苦行——管它是什么呢——付出了代价。也许,那其实是他心中的不安,是一个与周遭环境依然格格不入的外乡人的心态,总是轻装出行,这样等到他需要告别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将外套一把甩开。他以为就是这么回事,天太冷了。他穿得不够,出于他个人的愚蠢理由,而这场严寒让他抑制不住地打起了冷战,由内而外地瑟瑟发抖,让他觉得自己的身子骨眼看就要散架了。他站在公交站台上,不知所措,听着自己的呻吟,明白自己的意识开始恍惚,就好像他打了片刻的小盹儿,刚刚醒过来似的。他强迫自己动起来,可他的胳膊和双腿却像是没了骨头,他的呼吸声像是短促、沉重的叹息。他的双脚像是灌满了铅,失去了知觉,冻僵的血肉裂开道道缝隙,针扎般的痛。也许他应该坐下来,等待这一阵发作过去。可是不行,那样一来他就得坐在人行道上,被人当成是流浪汉,他也有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强迫自己往前走,艰难地迈开步伐,一步接着一步。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回家,赶在他的气力耗尽之前,赶在他倒毙旷野之前,他的尸体会在原地就被撕成碎片,散落各处。从公交车站回家的路他通常要走七分钟,约摸五百步。他有时候会数,借此淹没脑海里乱哄哄的声音。可那天傍晚,这段路一定走了不止七分钟。他感觉似乎走了不止七分钟。他甚至都不能确定他还有没有力气支撑下去。他好像从一些人的身边走过,有时候他会打个趔趄,不得不得找面墙,倚上几分钟或是几秒钟。他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他的牙齿在打颤,等到他终于摸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已经一身大汗了;他一打开门,就坐在了门厅里,任由燥热和眩晕将他压倒。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
他的名字叫阿巴斯;尽管他自己没有察觉,但他进门的动静其实很响。他的妻子玛丽亚姆听到他在摸索钥匙,接着又听到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而换作平时他都是悄无声息地溜进门的。有时候,玛丽亚姆甚至都不知道他回家了,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一脸微笑,因为他又逮到她了。这就是他爱开的一个玩笑,总爱吓她一跳,而她又总是被他吓着,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进门。那天傍晚,钥匙插进门的声响惊动了玛丽亚姆,对于他的归来她感受到了片刻很是平淡的喜悦;紧接着,大门砰的一声响,她听到了他的呻吟。她出屋来到门厅,就看见他坐在地板上,挨着门口,两腿在面前摊开。他的脸被汗水打湿了,他的呼吸困难,气喘吁吁,他的双眼迷茫地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阖上。
玛丽亚姆在他的身边跪下,叫着他的名字:“噢,不,阿巴斯,阿巴斯,你这是怎么啦?噢,不。”她把他那只滚烫潮湿的手放进自己的手心。她刚一触到他,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他张着嘴,费力地喘着气,她看到他的裤管内侧已经湿了。“我来叫救护车。”她说。她感觉到他的手轻轻地握紧了自己的手,过了片刻他呻吟着说了句:不要。接着他又低语道:让我休息。她身子后仰,跪坐在脚后跟上,他的无助让她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他的身体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与恶心中起伏着,她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握紧了他的手。又过了一小会儿,她开始感觉到他的躁动在平复。“你做了什么?”她柔声问道,喃喃地问着自己,喃喃地问着他,“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她觉察到他努力想要站起身来,于是将他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帮助他挣扎着爬上楼梯。不等他们走到卧室,他就又开始浑身战栗了;玛丽亚姆承受住他的体重,硬是架着他走完了上床的最后几步路。她匆匆脱去他的衣物,擦了一把他身上沾染秽物的部位,再给他盖好被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先给他宽衣擦身,再给他盖被子。也许这只是一种敬重身体发肤的本能吧,一种多余的、她从来没有多想过的礼仪。忙完这些后,她在他的身边躺下,卧在被单上面,而他则在一旁一面发抖,一面呻吟,一面出声地啜泣,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不要,不要。等到阿巴斯终于不再战栗,也不再啜泣,甚至像是睡着了的时候,玛丽亚姆便回到楼下,拨了诊所的紧急电话。大夫在接到她电话后的几分钟内就现身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那位大夫是玛丽亚姆从未在诊所里见过的一个年轻女人。她脚步匆匆地进了屋,面带微笑,态度友善,仿佛这里并没有出什么特别吓人的事情。她跟着玛丽亚姆上了楼,瞥了一眼阿巴斯,然后环顾四周,想要找一个地方搁手提包。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深思熟虑的,好像是在告诉玛丽亚姆不要恐慌,而既然大夫已经来了,她也确实感觉自己镇定了不少。大夫给阿巴斯做了检查,测了他的脉搏,用听诊器听了他的呼吸,量了他的血压,拿灯照了他的眼睛,又取了他的尿样,往里面放了一张石蕊试纸。接着她又问他问题,问他出了什么事,有的问题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他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她的声音与举止中透着的不是担心,而是礼貌与关怀;她在和玛丽亚姆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甚至还抽空和玛丽亚姆相顾一笑,她的牙齿闪亮洁白,她深色的金发在卧室的灯光下泛着光。他们是怎么学会这一套的?玛丽亚姆不禁疑惑。他们是怎么学会如此从容淡定地处理受伤的人体的?就好像她面对的是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似的。
大夫叫来了一辆救护车,等到了医院他们告诉玛丽亚姆,阿巴斯犯的是糖尿病急重症,还没有达到昏迷的程度,但也够严重的了。他们告诉他,这是迟发性糖尿病,出现在步入衰老的人群身上。通常这病是可以治疗的,可他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之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因此发展成了急重症。现在要完全说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还为时尚早。他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吗?他的父母、叔伯和阿姨有得病的吗?阿巴斯说他不知道。第二天,专科医师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说,糖尿病不会危及生命,但从他的运动反应[1]来看,他的大脑可能受到了某种损伤。没必要如临大敌的。他有可能还可以恢复部分丧失的功能,也有可能恢复不了。时间会给出答案的。他还得了轻度中风。常规检查可以明确他的身体情况和对应疗法,但在此期间他得再留院观察一日,如果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状况,那他就可以回家了。医师给他开了一份长长的禁忌清单,让他服药,又叮嘱他要请病假,别去上班。这年他六十三岁,而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
1 一天
2 搬家
3 逃跑
4 归来
5 仪式
译后记
附录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获奖演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