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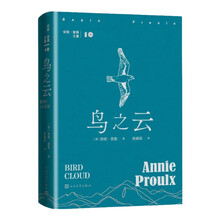


广场左侧被宫殿教堂投上了一层阴影,两座塔楼的影子一直延伸到纪念碑外。右侧则是通往宫殿花园的凯旋门,两扇富丽堂皇的锻钢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洒满阳光的笔直的林荫道,看到那里众多由砂岩建造而成的、肢体歪七扭八的雕塑,以及人造瀑布。一个保姆正推着一辆婴儿车穿门而过;这在过去是被禁止的,因为婴儿车及其内装的下流胚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体面的宫廷区域。小姐一时之间忘了,连统治者家族也会繁衍:人上人不可以再和人性的东西有关联,社会阶层越低,小姐心想,丑陋的性冲动就越是活跃。纯净高于不纯的分层被世界的民主化摧毁了,就算小姐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她知道,在一个有序的国家绝不允许一位淑女被一个下层人穷追不舍。宫殿前昔日曾设有双人岗哨,他们仿佛仍在守护着这里,因此小姐觉得安心了一些:一名摄影师在宫殿入口处架起了照相机,相机上盖着一块黑布,等待着想和骑士立像合影的异乡人,—勉强算是对哨兵的替代;小姐觉得安心了。她径直穿过广场向教堂的台阶走去,确信跟踪者没胆量把自己的无耻企图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能在广场边缘盯着她。确实,她身后的脚步声停了下来,然而她仍然不可以把头转过来确认一番。由于强撑着不回头,她的脖子痛了起来,仰望上帝和卷云所在的高空也没得到缓解;但她还是有点感激,因为危险已经解除。
只是那个男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他不是—回忆此时显然更清晰了—佩戴了一枚党章,而且是枚金色党章吗?如果属实,那他可能是纳粹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肯定不是共党,难怪他这么放肆。总的来说,自此纳粹掌权以来,他们的粗俗放肆就越来越昭然若揭。他们是衣冠禽兽:无论如何,她不愿意再想那个人,她也没必要再想他。
但她走进教堂,想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她再次感到自己脖子紧绷,感到了自己背上那道火热的目光。她犹豫不决地停了下来;被一个目无上帝的人的目光污染,被这个目光吸引,无法摆脱、无法忘却,如果这时还去参加祷告,那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教堂里满满的人,反正也来晚了,完全可以逃出去。小姐在人群中缓慢地往前挪动,向着侧厅走去,那里的地面上铺着石子,走路时如果踮起脚尖,声响比在中厅这里的木地板上要小。接着她经过柱子,来到以前供王公贵族出入的侧面出口,无声地推开装了软垫的门,当它轻轻地、像是屏气叹息一样地在身后关上时,她也轻舒了一口气,她抓了抓自己的脖子,就好像要拂去什么一样,也像是要揉一揉疼痛的部位。她来到了教堂和宫殿侧翼之间的小院中,真是解脱啊,在这里真真正正只有她一个人。小院像个没有房顶的前厅,严肃而又庄重,宽阔的路面嵌了一层特别平整的方形石块,麻雀疑神疑鬼地来回蹦着,实际上什么也找不到。有一把长椅的话,就可以待在这儿,尽管此时从教堂里传出的平缓的合唱声像是一种警告。小姐犹疑地穿过敞开着的、同样庄重严肃的双拱门,来到宫殿广场,并用近乎狡猾的眼神环视着广场。摄影师还在老地方,纪念碑旁站着一对夫妇,显然是外国人,旁边走过几个女人。此外别无旁人。也就是说,她施计骗过了跟踪者,她甚至骗过了上帝,因为她现在望向了先前不可以望的地方;为了看看身后,她绕了个圈,如今成功了。不,现在已经没人在她的身后了,尽管她的脖子仍能感受到那道目光,火热的目光;似乎是想一劳永逸地做好防护,彻底地清除身后所有不确定、所有晦暗的危险,她倚在了两道拱门之间的柱子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挪到柱子附近、后背能感觉到背阴的石墙所散发出的凉气的地方。她不可以倚在这里观赏这美丽的广场吗?她不可以倚在身后背阴的庭院与面前洒满阳光的广场之间的分界线上吗?很多人都曾经在此处或是那边的教堂台阶上欣赏过广场的风光,曾经望向那些花园,花园的林荫道消失在丘陵的下坡处,而现在纪念碑旁的那对夫妇也走了过来:他们的腿并排着前行,四条腿,扛着两个头颅和两具身躯;丈夫手拿着一本红色的旅行指南。摄影师的器材立在三条腿上,纪念碑上那匹马有一条弯曲的腿悬空,扬蹄向着蓝天;天空低垂在花园之上,被沉浸并迷失在下方的无限中的大地所吸引。那个美国丈夫翻开了旅行指南,他的妻子也看过去,看向那些字母,两人的目光在它们身上交汇。
行走于林中之人,有能力摆脱邪恶,因为魔鬼跛足,再狡猾也只能直行,因此到头来终被愚弄。
小姐倚柱而立,万一追踪者出现在小院中—但他没有,唉,他肯定不会出现在那里—,他也不会看到她,因为柱子把她挡得严严实实。但是现在她拿着赞美诗集的手垂了下去,而且由于她觉得有一点虚弱,她便向柱子的边缘伸出手去;她只是碰了碰冰凉的边缘,只用小指,而且可能并不灵活地碰了碰,因为黑色封皮的赞美诗集此时打了开来—啊可怕!—跟踪者眼镜片后泛红的眼睛很可能不只看到柱子边缘的手指和打开的书,而且还会辨认出书上的文字!小姐迅速地抽回了手和书。只不过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本神圣的书难道无法驱赶那个恶人吗?还是她害怕,那人更为强大,他的目光会使这本书的神圣性丧失?她是在害怕婚姻,害怕魔鬼的婚姻,害怕自己的目光与他的交汇于字母之上吗?啊,他不能碰她的手,否则这一切就会发生!
宫殿中部山墙处的旗杆上挂着纳粹的卐字旗—背弃传统的象征。没有风,卐字旗一动不动地垂在旗杆上,这条狭窄的红线,被蓝天衬托得分外清晰,上面的那缕红突然与不远处那两名游客手中的红色指南联系了起来,彼此结合,一起向里看着,两处都是暴发户的红,都引人堕落。
拱门下,麻雀叽叽喳喳。夫妻俩离她更近了;他们结了婚,因此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来观赏椭圆的广场,缅怀建造它的公侯;他们觉得正常,他们刚刚从自己的红色指南中获悉,这是座美丽的建筑。院子里的跟踪者是个下等人,但是她摆脱不了,着了魔似的倚在柱子上,像个丐妇。小姐现在又把赞美诗集抵在了身上,但她同时也清楚,被书抵着的那颗心,无法破译那些文字,黑色封皮下的白纸上写着的只不过是些字母。天空的圆反映在广场的圆中,广场的圆反映在围着纪念碑的圆圈中,天使的歌声反映在从教堂里传出的歌声中,而教堂演唱的歌曲就在她心口的这本书里,但是人们必须知道这些,必须知道,上帝反映在王侯中,王侯反映在穿越广场的凡人中: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那纪念碑周围的圆就永远不会成为天空的圆,赞美诗集中的词句永远不会变成天使的歌声,那时就可以推着婴儿车穿过公园门,而且令人愤慨的,竟不会有人以之为忤。婴儿车是黑色的,像黑色的摄影器材了无生气的目光那么黑,这道目光把一切都固定在相片中,啊,固定,从而使它们泾渭分明,使天地分开,恰如神在第一天发出的命令,分开,却仍然统一于神之道。
救世主从上界降临,集神性与世俗于一身,这样一来,他,成了肉身的道,就能用人类的语言来宣布神的真理,作为深受肉身之苦的祭品为尘世赎罪。反叛天使同样也从天上降落,却跌入火红的邪恶深渊,继而以人的形象爬上来,虽然彻底摔瘸了腿,却更加贪婪地追求与人子的肉欲之欢,而人因为俗世的弱点一次次地遭受着诱奸,屈从于强暴的诱惑,巫师和巫婆,与成为肉身的罪恶联姻,当然也像它一样沉迷于清除,并且最终无力招架赎罪的行动,但一次次威胁着后者,并把邪恶一代代地传下去,直到末日审判。
然而,每一片云不都是地与天之间的使者吗?它不是在溶解大地,拉下天空吗?这样一来,天空的圆就可以挤到房屋和广场的围墙之间,并挣脱出去,挣脱出这仿制的不可饶恕的圆。墙是白的,先于黑压压的云层飘来的云是白的,书和书上的字词是黑的,但目光火红灼热,从漆黑的眼窝里射出,吸收着自我,不断后退,穿过使人失去行动能力的死亡之门,不断后退,进入黑暗的刻骨寒冷中。公园笔直的道路彼此纠缠,绕了一个又一个的弯,缠成了一个淫荡的线团,其中的一切都一模一样,彼此纠缠,相互吞噬,又不断地孕育彼此。此时岗哨没了用处,一本红书力求反映熊熊燃烧之物也毫无用处,因为大反映于小已被抛弃:美好的事物和美均被抛弃,纪念碑上的马匹冲出了其凝固的美,飞奔而去;人的肺在教堂的回声中窒息,没有相片可以再固定住发生的事情,因为最大的秘密突然迸发,喷涌到公共广场之上。小姐伸开双臂,甚至向后伸去,依着、紧贴着柱子,这是她眼下唯一的依靠,她紧紧地抓牢,不再担心跟踪者可能会抓住她,拉着她的胳膊往回走,把她拉到自己身旁、拉到他所在的深渊,也丝毫不考虑自己的黑色大衣会沾上污垢。拱门下麻雀的叽喳声越来越聒噪,变得如鸣笛的呼啸一样响亮;阴影已经移走,就好像所有的遮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任凭已经不能再称为世界的世界令人难以忍受地一丝不挂,成为暴发户和引人堕落者的猎物,魔鬼的猎物。
无法逃脱的强暴!在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魔鬼的线团跳起了圆舞,无影的瘸腿舞,跟踪者很快就会低三下四地跛足而来、低三下四地鞠躬邀她共舞,无法逃脱他的诱奸。
此时,那对外国夫妇,仍然是四条腿,已经来到了教堂的台阶上,手中依旧握着打开的旅游指南,两人甚至准备闯入小院。可能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就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发现那里的秘密和耻辱,发现获胜的跟踪者;大概无关紧要了,因为现在已经没了任何遮蔽,连那座院子,那座曾有一个出身低下,却仍然如纪念碑一样矗立于中央的男人站立和发号施令的院子,都没了遮蔽。或许是为了保护跟踪者—她从现在起注定永远是他的牺牲品和床伴—,她准备施展巫术,或许是想趁着还来得及和他一起逃跑,或许是要把他藏在衣柜里,免得被两个陌生人发现,小姐极力从墙边挣脱开,转身走向小院:但是—唉,失望,同时如释重负—背阴的院子依然空荡荡的,一如她离开时的样子,麻雀仍在铺路石上蹦跶。四堵墙围住了这个四方形的院子,严肃冰冷,像朗朗晴空温和地转暗,对于一个下等人、共产党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这里没他们的空间。院子干净得连鬼都没有。
此时小姐再次鼓起勇气回望了宫殿广场一眼,那里也干净得连鬼都没有一个。因为无人跳舞。旗杆上的旗松松垮垮地垂着,强暴再一次被击退,或许只是被延迟,但今天肯定已被击退。小姐的灵魂中升腾起一种惋惜的幸灾乐祸。的确,昔日和既成之物冷酷的美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战胜了卑贱的瘸腿恶魔和他的愚蠢丑陋。宫殿广场在庞大庄重的建筑物前伸展成一个美丽的大椭圆,反映着天空的圆和静谧,—一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体验;塔楼的影子现在勉强只能遮住纪念碑的小小椭圆,选帝侯的马三脚而立,有一种僵硬的美,摄影师的三脚架也是三脚而立,花园的林荫道投下一线漆黑笔直的影子,沿着山丘一路下坡,笼罩其上的是浅蓝的穹顶,卷云正缓缓飞过,—纯净,高于所有的不纯。
教堂里传出合唱声。小姐满怀忠贞,穿过小院,进入教堂;她所穿过的门正是昔日大公一家去做礼拜时所走的那扇,而今,蒙神的旨意,她将不断地从这里经过。小姐的一部分灵魂不需要再和另一部分交谈,两部分的声音如此和谐统一,使得她满怀着甜蜜的无望感,几乎无法再想到自身:她像修女般打开了赞美诗集。
声音的寓言 001
声音:1913 007
Ⅰ 伴着微风启航 015
Ⅱ 条理的构思 030
声音:1923 045
Ⅲ 浪子 050
Ⅳ 养蜂人之歌 087
Ⅴ 女仆策琳的故事 098
Ⅵ 惘然若失 131
Ⅶ 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的四次演讲 150
Ⅷ 老鸨之歌 187
Ⅸ 买来的母亲 201
声音:1933 257
Ⅹ 石客 270
Ⅺ 乌云飘过 308
成书记 321
在地狱中寻找家园 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