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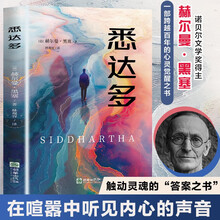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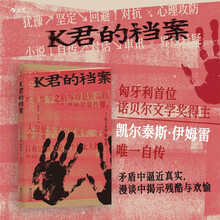




《布劳迪小姐的青春》作者缪丽尔·斯帕克颠覆犯罪小说传统的中篇代表作
以宗教般的狂热阐释人类固有的“罪恶意识”、“亵渎意识”、“厌世意识”
作家化身上帝的间谍,冷眼看人物跌跌撞撞走向毁灭
英国爵级司令勋章获得者、《泰晤士报》“1945年以来的50位英国伟大作家”名单
第七章
当她回到汤姆森旅馆的时候,已经半夜三更了,整条街都关的严严实实的,只剩下这家旅馆还醒着似的。莉丝把这辆小黑车停在门口不远处,拿着她的书和拉链包进了酒店前厅。
前台剩下一个夜班值班人员,制服从上数三颗扣子都解开着,露出脖子和里面的背心,也说明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大部分游客早已熟睡了。前台值班人员正在电话上跟某间客房通话。与此同时,前厅仅剩另一个人,一位身着深色西装的年轻人,站在前台跟前,一个公文包和一个格纹呢子的旅行包放在一侧。
“请别叫醒她。这么晚了完全没必要。把我的房间指给我就……”
“她已经下来了。她说了让您等她一下,她已经下来了。”
“我早上见她就行了,完全没必要。这么晚了。”该男子的语气带着专断和懊恼。
“她完全没睡,先生,”前台解释,“她非常明确:您一到我们就立刻通知她。”
“劳驾,”莉丝略过西装男士对前台说,“你要不要看这本书?”她举着手里的书,“我用不着了。”
“哦,谢谢了,小姐,”前台一团和气地接过书来,举得老远以便看清书名。这时这位刚抵达的顾客,被莉丝挤到一侧,侧身看她。他大惊,弯腰去拎他的行李。
莉丝拍了拍他的胳膊,“你跟我来。”她说。
“不,”他一个激灵,圆脸白里透粉,因为恐惧眼睛睁得老大。他的商务西装和白衬衫利利索索,就像早上莉丝跟着他、坐在他旁边的时候一样。
“放下东西,”莉丝说,“赶紧,不早了。”
她敦促他走到了门口。
“先生!”前台叫住他,“您的姑妈正在下楼……”
莉丝扔挟持着她的男士,在门口转身回应,“你先保管他的行李。你也可以把书留下:这是一本悬得不能再悬的犯罪动机小说,中心思想是别跟你不能撂在客厅地板上留给佣人收拾的那类女孩搭讪。”说完她继续领着她的男士往门外走。
此刻,他还在挣扎,“我不想去。我想留下。我今天早上就在这看见你了,我立刻离开了,我想离开。”他试图挣脱出来。
“我有辆车停在外面,”莉丝说着推开狭窄的旋转门——他像是被逮捕了一样。她把他带到车前,松开他的胳膊,自己钻进车里坐到驾驶座上,等着他从另一侧上车,坐在她旁边。然后她驱车和他离去。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你。”
“这不是重点,”她说,“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你浪费了我的时间。这一整天!而且我一开始判断就是正确的。从早上我看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你对我的路。”
他瑟瑟发抖。她说:“你之前在一个诊所里。你叫理查德。我是从你姑妈那知道你叫什么的。”他说:“我接受了六年的治疗。我想重新开始。我们全家都等着见我呢。”
“诊所里所有房间的墙是不是都刷成浅绿色?一到晚上是不是就有个彪形大汉在病房门口来来回回巡逻,以防万一?”
“是的。”
“别抖了,”她制止他,“你那是精神病院后遗症。马上就过去了。你到诊所之前在监狱待了多久?”
“两年。”他回答。
“你是用绳子勒的还是用刀捅的?”
“用刀捅的,但她没死。我从来没杀过女人。”
“没杀过,但你想杀。我今天早上就看出来了。”
“你以前从来没见过我。”
“那不是关键,”莉丝说,“不过是顺嘴一提,关键你是个性欲狂。”
“不,不,”他说,“那都是过去,都过去了。现在不是了。”
“你在我这是没性可言的,”莉丝一路开过公园,然后右转朝亭子开去。所见之处一个人影没有。之前溜达的人群已荡然散尽,车子也都开走了。
“性已经正常了,”他说,“我已经被治好了,性已经可以了。”
“当时确实还可以,之前也还可以,”莉丝说,“问题在于之后。这么说吧,除非你就彻底只是个动物,否则大部分的时候,之后都挺难过。”
“你害怕性。”他语气几乎有点愉悦,似乎感到一个控制局面的机会。
“只怕之后,”她说,“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她停在亭子跟前,看着他,“你抖什么?”她告诉他,“马上就结束了。”她伸手拎过她的拉链包,打开来。“现在,”她说,“咱们把话说在明处。这是你姑姑给你的礼物,一双拖鞋。你可以晚点再拿。”她把拖鞋扔到后座上,又掏出一个纸袋子。她往里面看了一眼,“欧珈的丝巾。”她说了一句,又把袋子塞回去。
“不少女人都是在公园里被杀的。”他靠在座椅靠背上,他已经平静下来了。
“是的,当然,因为她们自找的。”她还在包里摸索着。
“别太过火。”他平静地说道。
“那就看你的了。”她说着掏出另一个纸袋,朝里看了一眼拿出那条橙色丝巾。“这条是我的,”她说,“白天看颜色很好看。”说着她把丝巾挂在脖子上。
“我下车了,”他说着推开他那侧的车门,“走吧。”
“稍等一下,”她说,“就一下。”
“很多女人都被杀了。”他说。
“是的,我知道,她们自找的。”她拿出那个长方形的包装盒,撕开包装,打开盒子,里面是那把套在刀鞘里的裁纸弯刀。“另一份给你的礼物,”她介绍说,“你姑妈给你买的。”她把刀从盒子里取出来,随手将盒子扔出窗外。
他不同意,“不是的,她们并不想死。她们还是挣扎的。我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杀过一个女人,从来没有。”
莉丝开门下车,手里攥着那把裁纸刀。“走吧,时候不早了,”她说,“我看好地方了。”
曙光即将降临,到那天晚上,警察将会在他面前摊开那张地图,图上那座著名的亭子的小图标上打着个叉。
“你做的标记。”
“我没有。肯定是她自己标的。她轻车熟路。她直接把我带过去的。”
他们会逐渐透露给他,一丁一点地:他们早就掌握了他的案底。他们会冲他咆哮,他们会在桌子面前交换位置,他们会进进出出这间小办公室——他们一直被不安和恐惧困扰着,甚至在她的身份和来路被核实清楚之前。他们会掩饰自己的沮丧、尝试和颜悦色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已有的证据似乎都在证实他说的是真话。
“上次你失控的时候,不也是开车把一个女人带到郊外去的?”
“但这次我是被带去的。她逼我去的。她开的车。我不想去。我碰上她纯属偶然。”
“你以前从来没见过她?”
“第一次见是在飞机上。她坐到我边上,我换了座位,我当时很害怕。”
“害怕什么?什么吓着你了?”
翻来覆去,一轮一轮的审讯,进展极为缓慢,总是绕着相同的问题打转,像蜗牛壳上的螺纹。
莉丝走到凉亭巨大的窗户前,贴在窗子上朝里张望,他跟在她身后。然后她绕到亭子后侧,朝篱笆走过去。
她说:“我就躺在这,你用我的丝巾把我的手捆上。我把手腕叠在一起,照规矩来。然后你再用你的领带把我的脚腕也捆上。然后你就捅我。”她先指着喉咙,“先捅这,”再指着胸前两侧,“这儿和这儿,然后随你便。”
“我不想干这事,”他直视她的双眼,“我没想事情会弄成这样。我的人生完全不是这么规划的。放我走吧。”
她把裁纸刀从刀鞘里拿出来,感觉着刀刃和刀尖,然后说不算太锋利但够用了。“别忘了,”她补充,“这是把弯刀。”她盯着手中刻着花纹的刀鞘,然后任它从指尖滑落。“你捅进去之后,”她说,“一定要往上转一下,否则可能刺得不够深。”她示意腕部动作。“你会被捕,但你至少还能幻想一下开车逃走的机会。所以事后别浪费太多时间盯着你的作品看,你干出来的作品。”说完她就地躺在碎石地面上,他拿起刀。
“先把我的手绑上,”她说着把手腕交叠在一起,“用这条丝巾。”
他绑上她的双手,然后她尖声短促地让他解下领带捆住她的双脚。
“不,”他说,俯身跪跨在她身上,“脚不能捆。”
“我一点性也不想沾,”她叫道,“你可以事后再干。捆住我的脚先把我杀了,再说别的。他们早上会来把现场清理了。”
不由分说,他高举着那把刀进入了她体内,高举着那把刀。
“杀了我。”她用四种语言重复着。
刀扎入喉咙的那一刻,她发出嘶喊,显然是在体验结局的最终一击,她的嘶喊被汩汩流出的鲜血淹没,他一刀刺进去,又拧了一下手腕——毫厘不差地按照她的指示。接着他四处随意下刀,然后站起身来,看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站在那儿看了一阵子,然后转身准备离去,又迟疑了一下,仿佛忘了她关照的哪一条。突然他扯下领带,又蹲下去把她的双脚捆在一起。
他跑向那辆车,还想碰碰运气,但深知他最终还是会被抓住,车子离凉亭越开越远,他眼前已浮现出警察局那间可怜的小屋子,警察咣里咣当地推门进进出出,笔录员在一旁噼里啪啦地敲着他那馁弱的口供:“她让我杀她我才杀的她。她说好几门语言,但都是让我杀她。她明确告诉我具体要怎么杀她。我本想开始新生活的。”他已经看到他面前的警察身上的纽扣闪闪发光,他们或冰冷地窃窃私语,或激烈地咆哮怒吼,他们制服上的警徽、肩章,等等,一切装饰无不发挥着掩护的功效,好让他们掩遮住那见不得人的恐惧和怜悯、怜悯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