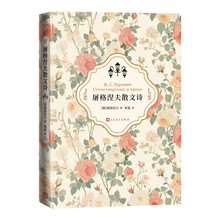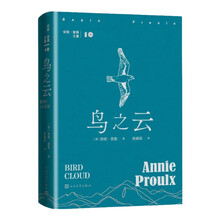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
在第三部分,关于“形式”,作者认为,“这部作品所包者广,它不仅是部想象的人物的传记,它还是全时代的写照;它不仅缕述出个人的思想,它还是对于整个时代各种思想(首先是文艺思想)的总批判,甚至我们就是称它是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欧洲文艺思潮批判史,也不为过言”。关于“造意”,作者分析说:“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之外,又创造了奥里维和葛拉齐亚两个人,这也是具有着深刻意味的,这正如同他拿德、法、意三个国家来做全书的背景,是同等地有意义。……罗曼·罗兰现在把他们(指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联系在一起,想用德意志的力量来救济法兰西的萎靡,用法兰西的自由来救济德意志的顺服……但这一切还不够,因之罗曼·罗兰又创造了葛拉齐亚,作为意大利的化身,作为美丽与光辉的实体……这也正暗示了罗曼·罗兰的三位一体的文化交流的思想。不用说,在今天看起来,罗曼·罗兰的这种造意是很有商讨的余地的,但他在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时,这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理想与尝试。”从作者上述见解中,当然也能看出傅雷《译者弁言》里的观点,作者显然是把傅雷《译者弁言》里的思想作为自己撰文时的重要参照的。不过笔者要对作者的“商讨”提出自己的商讨:我们不能用对待政治家的要求来要求作家。当一个作家,对人类有着美好的理想,并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时,即便这种理想显得不切实际,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因为,也很难说这种把人类引向至上、至善的理想,不能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追求。作家的任务是要给世人的生存打造更多的精神支柱,开耕更多的精神园地,拓创更多的精神向往。批评一个作家“没有能找到一条真能彻底消灭战争,为人类谋幸福,开辟新世界的历史行程所必由的道路”③,是把对政治家的希望寄托到了作家身上。
第四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它告诉读者“怎样来理解它”“怎样来接受它”。作者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它诞生的时代,是具有着现实的意义的。它对于当时的虚伪与暴力的社会,曾作了最有力的反抗,……更对当时一切的思想作了最有力的批判。而克利斯朵夫那种不屈不挠和与艰苦作斗争的精神,就是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是一种最好的鼓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中所发挥的英雄主义和对于自由的个性的渴求,是带着乌托邦和浪漫主义的性质的,而他更大的悲剧,就是当他呼吁人家起来和社会的不义及反动力量作斗争时,只能凭着良心作指导,用内心的宝藏——爱情、友谊、仁慈、道德的崇高的美来和它们对立,但这一切在现实的斗争中又是多么无力!……当我们今天来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时,我们应该记得,罗曼·罗兰本人在写完它时也是舍弃了它和超越过它的。”文章作者在道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接下来更多的笔墨,是提醒读者冷静地看待这部巨著,它不过是罗兰早期思想的反映,并引用罗兰写的《末卷序》来证明他后来思想上的“超越”:“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丢在后面,像一个空壳似的。生命是一组连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我们一起死去再生吧!”作者的分析不无道理,罗曼·罗兰的思想前后是有不同的,明显的转折是从1931年发表《和过去告别》始,而罗曼·罗兰的《末卷序》写于1912年10月,所以作者的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不能令人信服。罗曼·罗兰“与过去的灵魂告别”不等于说“与作品告别”,不等于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应当丢弃了。果此,为什么罗曼·罗兰对这部作品在苏联受到欢迎而感到格外兴奋和安慰呢?为什么罗曼·罗兰又十分关心它在中国的命运呢?但笔者的问题倒在于:为什么文章作者要提醒读者,《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的是罗曼·罗兰前期的思想,是罗曼·罗兰已经舍弃的思想?这背景因素中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约翰·克利斯朵夫》引起了万人争购和传阅,倾倒了无数的读者,越来越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大有压倒其他著作的“过热”的趋向。只有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都来竞相阅读这部名著宝典,对它着了迷的时候,才能有高层的有识之士,对这种“过热”的现象提出冷静的观点。青年人阅历少,看事情不够深刻,这是有识之士关心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戈文是一篇能全面评论这部巨著的文章。
翻译文学经典赢得了读者的热情,也继续推动着研究的热情,王元化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一篇评论文章。作者是我国的文艺批评名家,他并不从那种固定的评论模式来谈《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强调指出,“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谁能够抛弃那种文学ABC的滥调俗套,用自己的朴素的眼睛去看,谁才会领略到原作的真正的精神”;他还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合艺术规律”的“独特”的写法表示赞赏,“因为罗兰像一个音乐家,不是要创造‘物质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是要创造‘精神世界’领域中的现实”。王元化还对茨威格的研究视角提出批评,并质疑法国批评家布洛克的观点。茨威格是罗曼·罗兰生前的好友,布洛克也是罗曼·罗兰景仰的批评家,两人的观点和认识照理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因而在我国也被视为重要的理论参照。然而,王元化却自有主见,不盲从权威,他用自己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同样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