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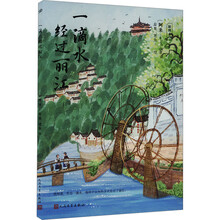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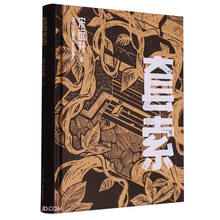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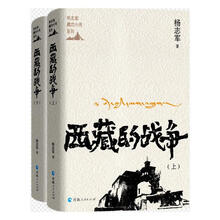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本书的主人公是上海家喻户晓的名演员于堇,舞台上她是美艳绝伦的红舞娘,舞台下她是西方情报机构的谍报人员。她时隔三年从香港回到上海,表面上是为了出演上海著名左翼导演谭呐的新戏《狐步上海》,也有人觉得她是为了营救自己被抓入76号的前夫倪则仁,甚至称她为“孟姜女”,但事实上她是为了得到日军偷袭美国军舰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被自己的养父兼上级休伯特召回上海进行谍报任务。在这座上海“孤岛”,山雨欲来,于堇在巨大压力之下,一边当好演员,一边与各方势力周旋,最终完成了任务,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上海的马路,像一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汩汩地流下去。下水道被泡过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
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与迈尔西爱路口。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信不信由你。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的确,没有多带钱。
票贩子在等票者中穿越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沓。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晚报说的!”
“绝对不可能!”
“怎么回事?”有人在急切地打听。
“这是谣言!”有人否认,那吼喊带着愤怒。
在戏该开场时,戏院门外的人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不少观众,中断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他们就是在家里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看事件如何发生,如何发展。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化妆,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他们挑战似的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
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观众们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觉得自己在受命运愚弄。他们的这份愤慨,像风中之火,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谭呐。
谭呐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上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谭呐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她已经离开人世。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谭呐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谭呐不得不对他们说话。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他尚不到35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辞,倾倒出心里想说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申报》记者在头版头条引用了导演谭呐的原话:“一个时代的结束!”。
她的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救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美丽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木架上。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