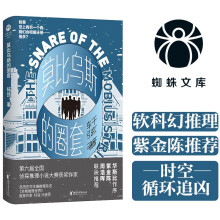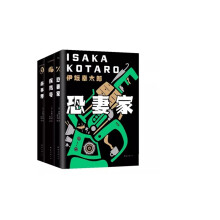《探寻“自我”: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研究》:
有评论者指出,简对“说”的渴望在于“她的言语看似被忽视或被强迫压制住时”。如果说里德一家忽视了简的声音,那么圣约翰没有爱的婚姻是罗切斯特没有婚姻的爱的重复,两者都使得简从他们所要求的“客我”中逐渐看到自我的实质,简学会了用“我必须说话”从他人的语言模式中脱离,改变了“客我”的困境,同时也尝试着用言说建构“主我”。
当人已经获得语言时,他就变成符号的创造者,而且不只是反映他的身体、他的自然环境或他的社会所提供的符号的人,同时在他说话时就得到一项新工具来达到他的目的,这时人与自我的关系就能够达到协调一致。在简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出现简与他人自由交谈的场景,每一个场景代表了简控制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不同阶段。
在盖茨海德经历红屋子的禁闭后,简意识到她最严重的疾病在于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灵上的痛苦,这时遇到了第一个同情的听众——家庭医生劳埃德先生,对方要求简讲述她不快乐的原因,但这并非易事,“孩子们能够感觉,可是不能分析他们感觉到的东西,即使在脑子里能够分析一部分,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分析的结果用言语表达出来。不过,这是我把自己的悲痛一吐为快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机会,我生怕错过”。对年幼的简而言.虽不知怎样准确表达思想,但也知道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讲述不幸遭遇的机会,她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使得劳埃德先生了解了她的想法,作为这次交谈的直接后果,简被送往劳渥德开始了学校生活。
在劳渥德学校,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当众指责简为“说谎者”,“一个外来的闯入者”,海伦和谭波尔小姐分别给予简一个理智地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当简认为人人都要以为她是撒谎者、坏孩子时,海伦和谭波尔小姐改变了简的看法,海伦说“只有八十个人听见他把你叫作撒谎者,世界上有几万万人呢”。谭波尔小姐说“你自己证明是怎么个孩子,我们就认为你是怎么个孩子”。谭波尔小姐要求简诚实地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允许她尽量为自己辩护,讲述过盖茨海德的童年生活后,谭波尔小姐认可了简:“简,在我看来,你现在已经是无罪的了。”这里展示了一个温馨的场景:使人感到舒适的房间、温暖的炉火、茶的热气、烤面包的香味,以及愉快的交谈。在这个场景中,叙述者着重描绘了海伦说话时的表现,在与谭波尔小姐进行交谈时,海伦的表现让简惊异得发呆,海伦心灵中的独特之处被激发:“她的心灵就像坐在她嘴唇上似的,话语滔滔不绝地流出来;我也说不出它是从哪个源头流出来的。一个十四岁的姑娘能有那么宽广,那么生气蓬勃的心胸,来容纳这纯洁、丰富和热情的雄辩的不断膨胀的源泉么?”如果将海伦与简做一个对比,从人生追求上来看,二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她们都希望寻求“家”来改变“流浪者”的地位。海伦是被父亲抛弃的孩子,她转而向上帝寻求寄托,“上帝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我爱他;我相信他也爱我”。而上帝所在之处,就是她永久的家、最后的家。海伦与简同样受不了学校里条条框框的束缚,同样在谭波尔小姐的房间感到自由,正如简对海伦戴着“不整洁”的标志感到愤怒,当简被宣布为“撒谎者”时,是海伦第一个来到简的身边支持她,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海伦也是一个反抗者,姓名海伦·彭斯有象征义:象征着被压制的愤怒,海伦的死是一种被动的自杀。在对“自我”理想的实现上,从谭波尔小姐房间的交谈中可以看出,海伦也希望用语言实现“自我”,海伦与简追求“自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实现理想的目的不同,简在现世寻找,海伦在身后寻找。作为简的对立面,苏珊.S.兰瑟曾指出伯莎使简的女性声音显得“有所依傍”,应该说海伦使得简实现自我的途径“有所依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