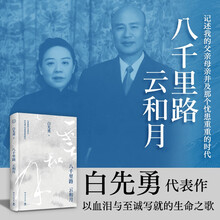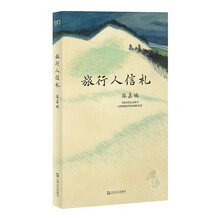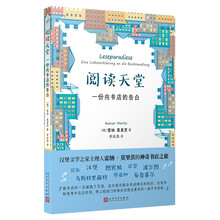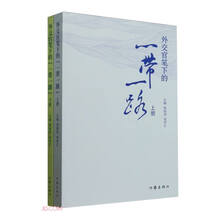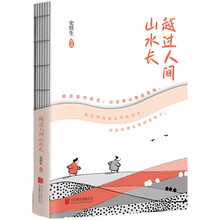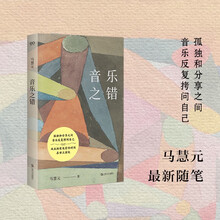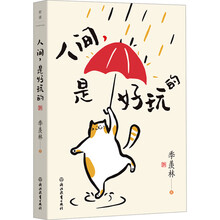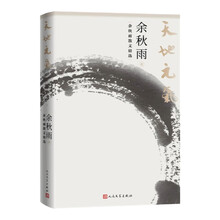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幽深之花》:
一座双港桥,将三河从传统意义上的水乡,往外拓展了一大步。双港桥下,除了流水,还有行船。船工们老远就望见这崭新的大木桥,以及桥边上的码头,他们便问:修桥者谁?
岸上的人听见了,便响亮地答道:桥庵众师父也。
双港桥边,桥庵又回归了宁静。桥建成了,尼姑们又沉进了木鱼声与诵经声中。只是经过桥上的人,总要侧头望望桥庵。修桥是功业,是大修;桥是修在河水上的,而修行则是存在人心上的。尼姑们只有在夜深之时,听着桥下的流水声,想着三河的繁华与清寂,脑子里如梦如幻如电,最后也都归于无声了。
这木头的双港桥存了多少年?问史书,没有记载。问现今的三河人,答不确切。但有一点他们都知道:桥修好后,每三五年,桥庵的师父们便用庵里辛苦化缘存下的一点银子,请匠人来修缮一次。桥事关人命,不能不修。但有一年,终于,她们没办法修了。那年春夏连阴,雨从三月一直下到六月。七月半,夜里,雨声如瀑,兼有大风。半夜,师父们听见桥身坼裂之声,与风声雨声混在一起。当家师父想出门看看,无奈雨势太大。等到天明,雨势渐小,出门,荒圩南埂上已空无一物。那耆老书写的“双港桥”三个大字,也随着流水,消逝不见了。河中,只有两岸边上还存着一两根木桩,整座双港桥,在这个雷大雨猛的夜晚,彻底被冲走了,河面上连一块桥板也看不见。尼姑们站在岸上,心中升起无限悲悯。她们无力重修一座大桥。她们双手合十。桥存在过,便也是这河上曾有的生灵。现在,它消逝了,那便得给它以发自内心的纪念。
多少年后,三河人都记得那个清晨,记得桥庵的师父们站在残桥边双手合十的景象。同时,他们将双港桥这个地名一直保存着,桥庵也一直陪着这残桥,度过了年年春秋。有私塾里教书的先生,便出了个谜语:叫桥不见桥,过桥不见桥。打一三河地名。桥庵的尼姑师父们,自然一猜就中。但从外地来三河的人,不免犯疑:既叫桥,为何又不见桥?既过桥,怎么能不见桥?
这谜语的上一句,说的是尼姑们建桥。桥毁了,只空留地名。下一句,便说到一百年之后了。双港桥被水冲毁后,因为桥身太长,投资太大,而且,河水湍急,桥容易被冲毁。所以,后一百多年,一直无人再动修桥的念头了。河对岸及圩镇之间往来,恢复到了渡船时代。直到1936年,在双港桥旧址上,才有了一座过桥不见桥的浮渡。
彼时,三河集镇兴旺。三县相交,货物贸易,商旅往来,犹如河水,滔滔不绝。虽然有摆渡船只联结两岸,但往来之不便,显而易见。商会便召集众人商议,最终决定在老双港桥处,新建浮桥一座。决定一出,四处响应,不几日,便购得木船多艘,陈于水面之上,船体以铁链相连。此桥修通,虽然行人过河须得多走几步上下河岸台阶,但已是极大的方便。1938年,日本人开着汽艇沿合肥进入三河。他们将大浮桥拆开,但八个月后,日本人便很快逃离了三河。三河水网密布,又邻近巢湖,是多路抗日部队的集结地。日本人腹背受敌,难以久留。大浮桥又进入过桥不见桥的情景之中了。
谜语一直在三河流传,但1954年的特大洪水,还是将大浮桥冲垮了。从此,双港桥真的没有桥了。水落石出,谜底呈现。
万物最终都将消失,唯有时间永恒。1760年的伟大的圆明园消失了,1760年的三河双港桥消失了。它们或许都进入了另外的时空,但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只想象得出时间——在时间的唱片中,唱针划过,却永不停留。
与双港桥同样,在三河空留着名字的,其实还有七座桥。它们分别是:沈家桥、马氏桥、油坊桥、木鹅桥、无蚊桥、国公桥、王小桥。连同双港桥,正好八座。八是中国民间最为吉利的数字。三河除了有八座古桥外,环绕着三河的,是八座古圩。这些古圩栉比于三条河的南北两岸。分别是五牛圩、大兴圩、五星圩、汪家圩、沙垱圩、杨婆圩、任倪圩、荒圩。八座古圩,八座古桥,如果细心一点,绝对还能从三河的建筑与布局中,寻找出更多的蕴含着“八”的意象。比如,那些老街上的石板条,是多少个八?古桥上的青石,是多少个八?包括太平军兴建的坚固的城墙,是不是也暗合八的玄机?人家门楣上的灯笼,是不是连绵成了无数个红红的“八”?那些桥下流水流过的日子,或许也永恒于“八”之数字的萦回之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