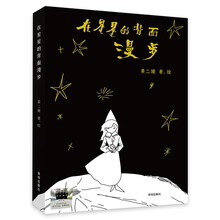田野上下,已经有人开始收割玉米了。我一时萌生出来的小冲动,丝毫没有瞒过妈妈的眼睛。她说,这些玉米是新品种,秆子没有一根是甜的。倒是脚下这些矮棵的猪草,村子里的人都掐回去,炒着吃,煮着吃,味道还不错。黄花香、苦马菜、小汉菜、灰苕菜、癞蛤蟆叶、缩筋草,它们正铺张地在玉米棵的脚下横行倒走。小时候,我的镰刀遇见它们,一把一把地收割进篮子里,像是收割满心满意的快乐。其中的一些野菜,我是吃过的,在城里的餐桌上,细细地咀嚼,即使是苦的,也能嚼出些甜味。那感觉竞与《诗经·大雅》中的“堇荼如饴”不谋而合。
堇荼是一种苦菜,与眼前这些生机勃勃的野菜,也许只是名字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救物主,饥荒时可用来饱腹,锦衣玉食时被用来识别新鲜。当一些走过的日子蓦然在某个时间点交集相遇时,就连甘与苦都像是对调了位置。
此时,我与妈妈悠闲地坐在地埂边上。过路的邻居递来一串葡萄,色泽诱人,我接过来,才想送到妈妈嘴边,忽然想起,妈妈是不能吃这东西的,马上又缩了回来。妈妈说:“你赶紧吃吧。”甜甜蜜蜜的汁液欢快地在我的舌尖上滑动,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对甜极度渴望的童年。是的,如今的甜蜜唾手可得。而眼前这些田野里的玉米秆子,却让我嘴里的甜蜜沾上了一些苦涩。
去年秋天,妈妈迅速消瘦九斤。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在长秋膘的时节,能躲过核桃、板栗和月饼们重重贴上来的高热量,真是不容易。秋天过去,妈妈已经瘦得连双下巴都不见踪影了。我开始着急起来,带着她去医院检查身体,血糖居高。连测数日,医生几乎可以判定妈妈得了糖尿病。
我不相信,妈妈也不相信。她对于每一次测量过后的数据都找一些借口,昨天怪吃了酒,前天怪吃了红糖鸡蛋。后来,但凡能对血糖有影响的食物都忌了,谨遵医嘱,再去检查,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开始对糖极度警惕起来。一些糖分含量较高的水果像是成了家里的敌人一样,被抛弃,被仇恨。
寻医,问药。辅助一些西医的药品,甚至还加入了民间的土法,终于把体重稳住了。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见瘦小的妈妈嵌陷在沙发里,睁着两只大眼睛像个孩子一样探询我今天的忙闲和心情。其中一只眼睛的黑眼球上已经蒙上一层雾了,医生说那是白内障,得等再严重一些做手术的效果才好。
晚饭后我泡了一壶茶。妈妈是爱喝茶的,我记得她年轻时常常喜欢在茶叶里放一块红糖。现在,谈糖色惧。民间给这种病取了个名字叫“富贵病”。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糖都吃不上,怎么会有人患上这种奢侈的病呢?居然尿糖了。我的妈妈,那些年在月子里都吃不上糖的我的妈妈!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和奶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双方火气都很大,互相埋怨对方把几斤红糖藏到哪儿了。她们甚至都发了誓,说绝不可能偷偷藏到娘家去。那些红糖在好些年之后现身了,它们放在顶楼的一个小矮柜里,已经与柜子里的绵纸融为一体了。要知道,那些稀有的绵纸是留给爷爷的后事之用。长年咳嗽的爷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在他七十三岁那一年,丢下我们走了。爸爸想起了那一柜子的绵纸,打开,便成了一柜子面容模糊的心痛。
许多年后,她们都还在惋惜。妈妈得理不饶人,埋怨奶奶,说她在坐月子期间都没得吃几口红糖水。奶奶埋怨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害家里白丢了多少钱。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吃不上糖,家里有月子婆了,要去大队上打个证明,花上一块五毛钱,才有三斤红糖的供应。村子里的人为了得到点金贵的糖,想了许多办法。关于这些,我已经颇有些印象了。
在秋天收玉米的时候,镰刀挥过的玉米秆子留下好长一截立在土地上。我和小伙伴去找猪草,砍下一根玉米秆子,尝尝味道。遇上甜的,用牙齿剥开皮,像吃甘蔗一样,一根根吃完。一不小心,嘴巴皮也会被割破出血,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对甜的渴望。吐一堆渣子在脚下,吃下一肚子甜蜜,再背起小箩箩继续找猪草。我们最快乐的事就是在哪里能遇见一窝窝绿油油的嫩猪草,镰刀一挥,像刚吃过糖一样安逸。
收割完玉米,村子里的婆婆们把玉米秆子收了回去,用清水洗净,用铡刀把它们铡细碎了,又放进碓臼里舂,汁汁液液就舀在桶里,放进一口大黑锅里,煮啊煮,然后用纱布过滤。经过一道道工序后,剩下些混浊的液体了,再用文火慢慢熬制,一些淡薄的糖稀就成了。红褐色的黏液,它们被称作“糖”。女主人把它们装进一只土罐子里,密封,待家里有了用场时再拿出来。
因为工序麻烦,所得甚少,村子里只有少数几个勤劳的主妇愿意下此苦力。有时,村子里的娃儿被狗咬了,需要煮个糖水鸡蛋补血、压惊,就要端着小碗去讨点糖稀。我吃过那种糖,淡淡的甜味,总是让人意犹未尽,还不如我和小伙伴们去田野里砍根甜玉米秆子嚼痛快呢。
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