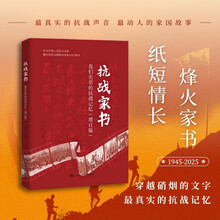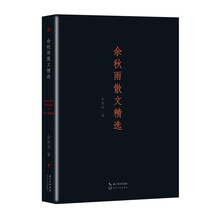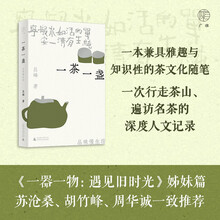在西安,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祝勇深感要找到一座100年以上的老房子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摩天大楼正取代被世代居住的古宅,改变了城市的结构与气脉,破坏了城市的文化和底蕴,除了给开发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并未为这座城市增添全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者成为古城的破坏者,在利益的引诱下欲罢不能。那个金戈铁马、风雅流丽的十三朝古都,已经随着拔地而起的新城市悄然消失。
在成都,承载着巴蜀世代生活方式和独特历史的宽窄巷子也将拆除的消息使祝勇陷入迷茫,在那里,他看到于时间的逼迫下,老房子一再退出自己的阵地,在自家老宅的废墟里打麻将的成都人,正在抓住最后的机会眷顾着老院的安闲,留恋着即将逝去的美好时光,挽留着世代养成的生活方式。
在广州,祝勇已经难以寻到西关大屋的线索和“西关小姐”的面容,他看到的,是工地、废墟以及新贵般的高楼正共同组成大开发时代的话语体系,以疯狂的态势向四周扩张,现实中的城市像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工地,以烟尘与噪声来炫耀自身的存在。
在昆明,在“最后的顺成街”,祝勇看到“最深的痛苦来自那些房子的主人”,因为“在这个无比势利的年代里,房子的主人早已被忽略不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们盗窃了别人的自由,连起码的客气都不表示一下,它们用君临一切的威严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在海口,老城虽因这个城市尚未为新城扩张做足准备而被暂时保留了下来,但祝勇看到一些新的建筑已被强加进去,连同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比如简单、方便、快捷,唯一缺乏的是审美,“它们以特有的话语方式对史诗进行改写,使其变得庸俗、实用和浅白,似乎在表明除了吃喝拉撒之外,生活再也不需要别的内容了。”
走访完上述城市,祝勇又将目光转向海外。在京都,他看到“固执里带着一股邪气”的京都坚守着古老的美,“从东福寺‘二门’楼顶向西北眺望,我看到大片的木屋参差罗列,仿佛大地上生长的树。京都是由树变的,所以整座城市都浸透着汁液的清香。”在纽约,这个“没有阳光的城市”里,他看到那些被摩天大楼挤出的“空中道路”彼此孤立,互不衔接,为了瓜分更多的阳光而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疯狂生长,同时又在水晶宫般的现代建筑外壳下,发现了一个隐藏其中的悠久、优雅的纽约——那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的老式洋房以及缠绕在花岗岩上的藤蔓和花朵所代表的纽约,在古老的街巷和各式各样的老房子中,他看到了建筑与大地、自然以及生命的联结,听到人与自然、与生命、与自我的对话。祝勇说:“将‘古老’一词用于美国,显得有些幽默,但事实是,古老的事物在纽约仍然存活着,精力旺盛。”
将视线重新转回到周遭,在目睹了太多残酷的现实之后,祝勇先生感慨:“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一样始终处于大规模的动荡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在始终转动着城市的魔方。”他对“以谁的标准进行全球化”进行反思,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谁来“化”的问题,如同所有动听的词汇一样,这也是全球化值得怀疑的地方。“作为一种专制,全球化旨在剥夺人们的选择的权利,人们将被迫接受一种强加的生活,作为交换,人们被许以某些好处。”却很可能又以某种隐蔽的方式残害人们,“因而,对于任何一种推荐而来的真理,我们都不应轻信。”抛开人们是否心甘情愿,抛开世道是否公平合理,那些以傲慢的姿态拔地而起的高楼又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祝勇先生说:“现代建筑则使人陷入一种囚徒般的生活——每个人被分割在封闭的空间里,楼房里没有公共场所,人们通过在空中乱舞的手机信号来传送信息。现代建筑表明了人类智慧的枯竭,人类没有找到一种安顿自身的更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对前人的智慧不屑一顾。”
当听到祝勇先生说:“对老房子的拆除通常是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居住者进行的一次巧妙的置换。”我再感同身受不过了,因为此时的父母和姐姐正在我的家乡为保不住自己的家和房子而心痛。姐姐购买的刚刚建了十几年的商品房和轮椅上的父亲含辛茹苦亲手建的自家的三层楼房都将被当作“棚户”,以棚户房远低于市场的低价被强行拆除、置换和改造,他们获得的补偿款将无法回购开发商即将在原址上重建的以市场价出售的商品房——如此的置换,实质不是剥夺又是什么呢?而此时,年迈的父亲和已退了休的姐姐也不得不为寻找自己安身的去处而操心和发愁。
我前不久回老家,看到我打小生活的县城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大拆大建之中,一边是开发者的欲望与豪情,一边是居家百姓的无奈与感伤,重返家乡的我,往昔的记忆也早已无处安放……我多年不见的老领导老局长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他广播局家属院的家也以不容商量的理由和补偿被拆除了,年过八旬的他和老伴被迫离开家园,曾为寻找新的住处四处奔波,一筹莫展,为此还生了一场病,至今精神失落,话语间流露着抹不去的伤感,腿脚也已有些不便。此情此景,唯有爱莫能助的无奈。
而我呢?下次再回家时,家也将再不是家,家再不存在了。
这些,都和祝勇先生通过十城的走访看到的情景没有二致。在古都西安,他看到不愿离开的老百姓请求政府允许他们自行修缮和保护世代居住的老宅,因为他们愿意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里,愿意与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对那些房子充满理解,或者说,他们与老房子是一体的,离开老房子,他们就像根须离开土地一样无法生存。”而那些已经写上的“拆”字的老房子,未来也将不出意外地只存在于文字和胶片里。在天津,当他在千疮百孔的老房子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他发现“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过去生活的顽固偏好,而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在北京,当他看到胡同口满含泪水的老太太,知道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遭到欺骗,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许诺成为谎言,居住者遭到背叛”。在昆明,在拆迁队的围剿下,78岁的老人和她的老姐妹们不走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因为“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50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