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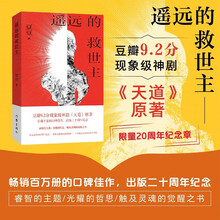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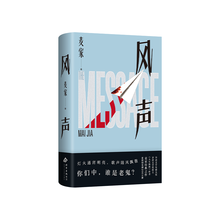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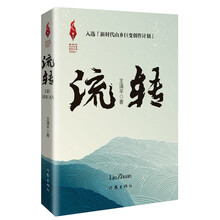
“阅读天津·津渡”丛书之《沽水升乡愁》,用文学解码天津的前世今生,一书纵览文学里的天津。
深度解析作家冯骥才、蒋子龙、林希、龙一、王松等天津作家的经典作品。
收录《神鞭》《潜伏》《乔厂长上任记》《十城记》《三寸金莲》《烟火》《暖夏》《天津闲人》等十余部津味小说代表作。
01 晚清的黄昏 怪影重重
学界有一种观点,晚清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国内最早以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晚清历史的,是已故天津作家、学者鲍昌先生。
1949年,随解放大军进城的鲍昌,刚满十九岁。他不属于“泥腿子”乡土干部,而是饱读诗书、才华卓异的年轻知识分子。后来他遭遇不公平待遇,赴农村改造。即使境遇艰难,鲍昌依然雄心勃勃,立下宏愿,写出多卷本的历史长篇小说《庚子风云》。1978年复出后,他曾以《芨芨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任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不久,他接到一纸调令,赴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庚子风云》的写作是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事。全书原计划两百万言,于1990年完成,惜乎鲍昌调任北京不足四年,全书仅出版了前两部,刚进入第三部的写作时,他却不幸患癌。1989年2月,他抱憾辞世,享年五十九岁。我甚至想,命中注定,“水土不服”的鲍昌,或许不该离开被他视为家乡的天津。
从已出版的《庚子风云》第一部、第二部看,全书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人物繁多、场景浩瀚、叙事飞扬、议论精辟,具有史诗架构和风采。天津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其前因与后果,起始与结局,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呈现。
天津晚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和市井气象,在鲍昌浓墨重彩的笔触下栩栩如生,颇有几分《清明上河图》的味道。
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学界一直争议不断,鲍昌更关心的是其中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大悲剧,是火与剑的哀歌,血和泪的碑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年轻人,应当温习这一段历史”。
天津是个民风独特的城市,此乃共识。不过,这个说法有些笼统,可套用于对任何一座城市的表述。有比较方有鉴别,其前提必须是各具特色、规模相当的两座城市。
张中行先生曾在《津沽旧事》一文中,以亲身经历,谈起对京津两座城市的印象,他认为“北京年老,文苑气浓一些”“天津
年轻,市井气浓一些”。两“气”相交,不同是显见的,却不宜刻意区分高下。世界上没有哪两座城市一模一样,大概率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具体到所谓的“文苑气”和“市井气”,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皆应顾及。
自元代开始,北京便是首都,历史悠久,资源优厚,名流云集,精英荟萃,底蕴如此深厚,“文苑气”想不浓都不行。天津源于“三岔沽”,人们沿河而居,渔人、船户、盐民、士兵,是早期天津的主要居民,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形成了水旱码头特有的民风,天津生活气、市井气浓一些,也很正常。
往往,学者聚焦的是正史和精英,作家关注的是野史和平民。冯骥才的小说视角,就是从老天津浓浓的“市井百态”切入的。
基于对地域文化的好奇和积累,冯骥才常常把目光投向晚清。这是大清帝国的黄昏时分,诡谲多变,坍塌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冯骥才很早就开始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症结,他注意到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与神秘的“阴阳八卦”现象,并将此梳理、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隐喻符号,分别指向文化的劣根性、人性的自束与精神的内闭,并将此具象化为故事与人物,植入小说文本。
汉族男人蓄辫,是清代独有的现象。比起汉族女人缠足,汉族男人蓄辫的年代并不久远,在当时怪异反常,必然会历经一番抵触和动荡。
只在脑后留铜钱大小的一缕头发,编成细辫子,细到能穿过铜钱孔洞,俗称“金钱鼠尾”。后来,允许辫子可以粗一些,变成“猪尾巴”,再变成“牛尾巴”。变来变去,总离不开牲畜尾巴的形状,稀疏且有碍观瞻。这还在其次,关键是必须剃发,否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神鞭》是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的第一部。小说的定场诗“古非今兮今非古,今亦古兮古亦今”,一上来就为“怪世”定了调。在清代晚期,男人蓄辫已习以为常。限于卫生条件,辫子很难及时清洗打理,男人本来就活得粗糙,辫子脏兮兮、臭烘烘是常态,外形近乎丑陋。冯骥才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化腐朽为神奇,变“奇葩”为经典,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嘉庆年间的一次皇会中,卖豆腐的小贩傻二登场了。引人好奇的是,他“头上盘着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好像码头绞盘上的大缆绳”,并以祖传的一百。八式“辫子功”,常常出头为弱者打抱不平。这“辫子功”出神入化,东洋武士佐藤自恃武艺高超,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傻二的大黑辫子打得在木桩上连转两圈。接下来:
“他(东洋武士)忽然见傻二的辫子一甩,像棍子一样横在自己眼前,东洋武士见这机会绝好,出手抓辫,指尖将将沾上辫子,这辫子又变成链条在他手腕唰地缠了两道。跟着傻二来个狮子摆头,硬把东洋武士从木桩上甩起来……”
傻二连续打败流氓恶霸和日本武士,“神鞭”威名,享誉津门。有些店铺,甚至把一条辫子威风凛凛地挂在门口,镇宅避邪。面对各方势力的暗算,书画家金子仙提醒傻二,“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之精神……你该视为国宝,加倍爱惜”。傻二顿觉责任重大,“好像脑袋后面拖着的不是辫子,而是整个儿大清江山那么庄严,那么博大,那么沉重”。这种联军的洋枪洋炮,自然不堪一击。傻二躲过死劫后方才醒悟,最后剪掉辫子,转而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
“神鞭”的故事,发生在一段愚昧、病态的历史时期,预示只有革除积弊,摆脱重负,适应变化,活着才有希望,这是小说的要义所在,也是一座城市在历史变迁中不断自我革新的隐喻。
此外,“玻璃花”的形象也值得玩味。天津是水旱码头,受漕运水手和船工中青帮的影响,总有一批好勇斗狠的恶棍欺行霸市。“混星子”现象是天津卫市井生活中的“怪胎”,这类形象不仅在冯骥才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在天津作家鲍昌、林希、肖克凡、王松的部分小说以及天津艺人郭德纲的某些相声中,也多有涉及。“混星子”不靠与对方互殴取胜,而是通过自残比狠,以获得“强势”地位。他们曾以“锅伙”的形式出现,最初也反清,属于哥老会分支,后来改变作风,以租借房屋为据点,故意招灾引祸,让对方暴打自己,只要皮肉能撑住,落个肢体伤残,便可获得霸凌一方的豪横资格。《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了解其害,四处捉拿“锅伙”,逮住便处死,这类现象随之销声匿迹。
《三寸金莲》是“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第二部。小说直指中国传统习俗的幽暗处,撕开了折磨中国女性身心长达几千年的伤口。
女子缠足始于哪个朝代?学界观点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陋习至少延续了上千年。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漫长历史中一路绿灯,畅行无阻,最先遇到麻烦,却是在清代。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禁止妇女缠足与强推男子剃发,两策并举,意在用满族习俗同化汉人习俗。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明令,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放偏远地区,却终难奏效。直至康熙年间,清政府见汉族女子缠足对其统治利大于弊,也就不再禁止。
冯骥才感兴趣的并非史实考证。他是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病灶的诊断者。小说中的香莲,奶奶对她百般疼爱,七岁那年给她裹小脚时,却如凶神恶煞。裹脚用的工具,居然是“炕桌、凳子、菜刀、剪子、矶罐、水壶、棉花、烂布,浆好的裹脚条子,卷成卷儿放在桌上,紧挨着几根大针,近乎刑具,看着恐怖”。裹脚过程,心狠手快,惨不忍睹。当香莲明白了缠足的“好处”后,竟主动配合,裹住了一双绝世小脚,日后嫁了人,还一次一次参加赛脚大会,享受了大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小说内核是荒诞离奇的,但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生活细节,却是用细腻、逼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描金贴丝般勾勒出一幅天津风俗画。
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采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章回体,行文仿似说书人娓娓道来,尽管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语言上却有轻松悦动之感,颇具天津独特的曲艺风味。小说发表后,或褒或贬,争议强烈,冯骥才本来也不期待一片喝彩,遂泰然处之,但读罢朋友楚庄写的一首小诗,“裨海钩沉君亦难,正经一本说金莲,百年史事惊回首,缠放放缠缠放缠”,竟生知遇之感,几至落泪。
《神鞭》《三寸金莲》一经问世,各种转载总数何止千百,译成外文亦超过二十种,《神鞭》更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文艺领域的“津味”代表作。冯骥才也凭此类力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遥相呼应,成为最早以“津派小说”享誉中国文坛的天津作家。
写《神鞭》时,冯骥才四十岁出头,正值盛年,笔墨近乎炉火纯青。如今年逾八十岁,笔力不减当年。他坦言,从小到老,在天津生活,心里踏实,精气神儿足,“我和这个城市的人们浑然一体。我和他们气息相投,互相心领神会,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交流”。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集五十八篇心血之作,借鉴了唐传奇的笔记体小说写法。小说素材大多源于津门流传的各类民间传说,有“三言二拍”的笔意与妙趣。细节写实,部分玄幻。人物俗与雅、奇与趣、闲与哏,相得益彰。其语言简约,半文半白,“津味”浓郁,视角刁钻。小说氛围的渲染、细节的夸张,都服务于笔记小说的内在张力。
老树新枝,再度醒目。此书荣获鲁迅文学奖,也是中国文坛的一桩美谈。
自序 文学的乡愁
01 晚清的黄昏 怪影重重
02 城市写意 从清末到民国
03 浮世绘 民国众生相
04 家族叙事 白雪与红尘
05 五大道的岁月镜像
06 不再尘封的红色记忆
07 风景延伸 改革年代的文学
08 津津有味 永远的乡愁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