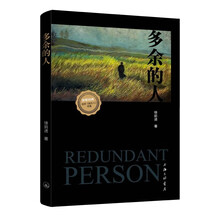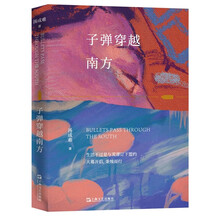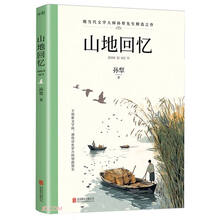甲申年的春天特冷。春寒之中重读鲁迅《春末闲谈》,品味着他对那种剥夺思想的治人之术的剖析,不禁怦然心动。因而联想到大学之失魂与我辈读书人精神之萎缩。那细腰蜂式的把戏,叫人“没有了能想的头,却活着”。我们确实是“活着”,但几人尚有“能想的头”?思前想后,觉得我们的教育大概是有病,是不是中了那细腰蜂的毒针?于是知识分子的“坏毛病”,便使我不禁生出种种像春寒般不合时宜的焦虑与忧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三年前我写过《失魂的大学》,去年又写了《再谈失魂的大学》,所虑之事依然存在,且有加剧之势。因又有几则随感写出,算是续篇。我倒是真心希望此种文字将无可再续,那时大学之真精魂便已归来也。
一、教育:“民爱”变“民畏”
在论及政治与教育的差别时,孟子有一个说法:“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现在的教育,似乎已经背弃了这则古训。你看,主其事者并不怎么措意于“得民心”的事,而是千方百计地忙着去“得民财”、乱收费、“搞创收”成为有中国特色教育的一大弊端。于是,本该是叫人爱的教育,便渐渐地叫人畏起来了。听说沪上民谣有“人民教师黑社会”之讥,北京则有百姓在民意调查中表示最恨两种人:教师和医生。这自然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情绪化表达,但其中的警世之意不可小视。应该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叫人民畏而恨之进而唾骂之?有一位朋友说,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在“教”界由“民爱”变“民畏”的同时,“政”界的人士却纷纷从大学里弄到了硕士、博士、博士后以至兼职教授、博导的美称,大大增加了从政的本钱,从而叫小民不敢不“畏之”,也不敢不“爱之”。有的政界人物,虽然一天也没有真干过教书育人之事,却宏论连篇,“指导”教育,俨然是一位大教育家了。而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够得上教育家如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者则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
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津制与“左倾”教条主义并没有随之而去。我们迎来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教育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那些最不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也就是官僚津制的“权”与市场运作的“钱”结了婚,迫使教育失其本义,叫人民望而生畏。具有启蒙思想的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绝其后。只有最短视、最没出息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只有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才派不懂教育的人去管教育。当然,完全灭掉中国的教育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十年“文化大革命”曾使教育几近灭绝,再往前推,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等。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异化、变质的蠢事,而是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势与金钱这两翼,不时幽灵般地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