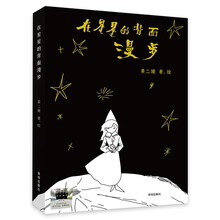大疫期间,足不出户。晚饭后有暇,就记忆所及,给家人讲解唐诗。每次选一家之作四五首,或绝句,或律诗,或古风,若是《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篇幅的一首也就够了。内容太简单的,或用典太繁复的,都不宜讲。抄几则稍成片段者,就教于方家。
王昌龄《听流人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第二句“分付”继以“鸣筝”,弹奏开始;第四句“收”上接“断弦”,乐曲戛然而止。二者之间有呼应关系。第二句与第四句各有一个“与”字,前一个是拓展,将“鸣筝”(题目中的“流人”所为)与“客心”(也就是诗人自己)联系起来,展开隐藏在字面背后的人生与世事;后一个是收束,将“千重万重雨”归结到“泪痕”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从大到小”。第一句诉诸视觉;第二句诉诸听觉;第三句既是视觉形象,也是听觉形象;第四句则从视觉(“断弦”)转为听觉(“收”),再转为视觉(“泪痕深”),一切都安静下来。可以说是“从动到静”。从第一句到第三句,其间有时间的变化(“微月”到“雨”),或许还有空间的变化(“枫林”到“岭色”),当然也可能只是目光由近转向远,所见景色由亮转向暗,“岭色”是形容迷茫一片。通常诗歌达成意境,往往是从小写到大,从静写到动,这首诗恰恰相反,所达成的意境却深邃而辽远,是因为诗中情感深厚,感官的广度浓缩成为心理的深度。然而这里描写感情非常克制。第二句有意隐去了“分付”的主体,而“流人”只见于诗的题目中,“流人”与“客”的身世际遇,均未著之字面;这一句中“客心”如同“呜筝”一样都是意象,却是当成一物来写的。只是到了全诗末尾,形容“泪痕”日“深”,才见情感色彩,正是恰到好处。“泪痕深”又呼应第二句的“客心”,虽是“客”之所见,却也深感共鸣。回过去看,第一句和第三句中的物象都带有主观因素,蕴含着“流人”与“客”浓厚的情绪。第三句既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的声音,也可以理解为乐曲之声。记得先父沙鸥先生曾说,诗的意境来自于形象与感情达到完全的融合,这首诗算得上是好例子。
贾岛《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唐朝诗人中,我自忖心境最相契合的是贾岛,他的诗概而言之,日空,寂,幽,冷。此诗中间两联,写了四个动作或变化,却予人静谧无声之感。所有的动作都是惯常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恒定的。颔联近观,颈联远望,此种静谧由局部展开至于全体。至于“推”“敲”二字哪个更好,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中说,推可以无声,敲不免有声;推只有僧人自己,敲则庙里还得有人应门。这些我都赞同;但他说“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那么冷寂”,我却觉得,敲有如前人之“鸟鸣山更幽”,而未必一定有人会来应门,只是期待而已,兴许久久不来,让人在那里空等。至于朱氏担心因此“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在我看来,这句的“僧”与上句的“鸟”仅仅是两个意象,彼此没有同在一个现实情景里的关系,类似诗人别处所写的“归吏封宵钥,行蛇人古桐”(《题长江》)、“雁过孤峰晓,猿啼一树霜”(《送天台僧》)等,只要这些意象共同达成所需要的意境就行了。
贾岛《客喜》:“客喜非实喜,客悲非实悲。百回信到家,未当身一归。未归长嗟愁,嗟愁填中怀。开口吐愁声,还却入耳来。常恐泪滴多,自损两目辉。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诗人有的诗意象丰富(不少五律的颔联或颈联,一句中容纳三个意象,如前引“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字斟句酌;有的诗(多是古风)则如这首《客喜》,直抒胸臆,质朴无华,上承魏晋诗、《古诗十九首》乃至《诗经》笔意。唐诗写旅愁的很多,很少如这首揭示内心和境遇到这般深切程度的。三四句,七八句,都刻画入骨,非有亲身体验不能道得。结尾归到一个细节,简直惊心动魄,且见出苦吟的功夫。杜甫《登高》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尾联“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都是类似写法,最后落到实处,以免写空泛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