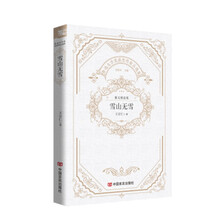踏空
我身上有几块疤痕,几十年了仍盘踞在原地,看来不会走了。这些伤痕的来历很让人后怕,它是踏空摔伤所致的。
我额头的伤疤,是缝过十二针的深痕。伤痕高低不平,是伤口太宽缝线粗糙的结果,是伤口太长难以长好的缘故,还是伤骨后难愈的沟壑,弄不清楚。我对这疤心有余悸。好在它紧贴发际,显痕有刘海遮盖,不然会明摆在额头。这疤虽无碍大雅,但因有人猜疑,便有了点自卑。
那摔伤的惨痛瞬间有多可怕,幸而幼时没记忆,不知有多痛。我妈说,吓死她了。她说,我从老高的炕沿往前扑,一脚踏空头落地,栽在三角石上,头破血流,人似乎没气了。她往血口抹了把灶灰,摸身上有丝温热,赶紧抱起就往医院跑。
医院在十里远的县城,在没车的泥路上,母亲抱着我边跑边走。我的伤口仍在流血,她磨破的脚也在流血和钻心地痛。一路奔跑的母亲,豁出命来往医院赶。跑到医院时,母亲看我额头翻绽的伤口不再流血,身上冰凉上涌,就地软瘫了。抢救的医生对我发抖的母亲说,人还活着,有救。她听医生说有救,身上又有了劲,眼泪却止不住了。
伤口缝了十二针。医生说,血快流干了,再晚点就没命了。妈说,她跑到县医院那么远,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母亲的述说,使我的泪水往外涌。母亲抱着我跑了那么远的路,哪来的力气,我想象不出来;母亲如在路上稍有停顿,我就没命了。
我懂事后,有几次母亲摸着我额头的伤疤,仍痛楚地述说那次的踏空。虽是重复述说,她仍在掉泪。我初听母亲讲那踏空的危险情形时,吓哭了。我不敢想我的那次踏空有多危险,我便在炕沿上比画当时踩空头栽地的境况,炕沿“告诉”了我一切,那惨状让我害怕。炕沿的松木滑溜如冰,触脚便滑;土炕比我高,对三岁的我来说是悬崖;地面有磨出来的三角石,它会“咬”肉,何况是嫩稚的额头撞它。难怪我一头栽地,便皮开肉绽。
我摸我额头的伤疤,再从这光滑的坑沿,瞅那地上的三角石,想那头栽三角石的惨状,心就抽搐,伤口顿现麻疼感。这麻疼感,原来沉睡在记忆深处,是被我模拟摔落的刺激唤醒了。可见当时头栽地,是无法形容的巨大疼痛,是刻在记忆深处的惨状。
这个伤疤,自从被我的模拟踏空唤醒,每当有东西触及到它,风雨雪刺激到它,甚至镜子照到它的时候,会有隐约的麻痛感。这使我有段时间常爬炕头愣神,好奇栽下去的情形。好奇的结果让我越发害怕。这炕的高,对幼儿确如摔落峭壁,即使大人踩空栽地,后果也难料。这使我每当想起那次踏空就心涌惊悸。
伤痕留在额头不愿走,照镜子会看到它,梳头会碰到它,不经意会摸到它,母亲常会端详它。我知道,最在意的是母亲,母亲端详它的那眼神,仍让我感到有揪她心的感觉。她在我长大,乃至离家多年后,仍会说起我那次踏空的险事。她常说我踏空的事,是在不停提醒我,抬脚有危险,走路得长“眼”,踏空会要命。
人走在山川江湖,不料踏空难防。
我的腿和胳膊有块伤疤,为掏鸟摔伤。那次上树掏鸟,张六娃让我踩他肩膀爬上去掏。我没掏到鸟,张六娃就不情愿给我当“梯子”。
P1-2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