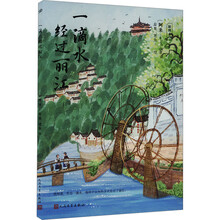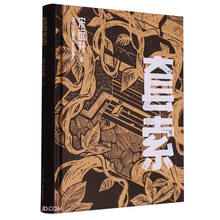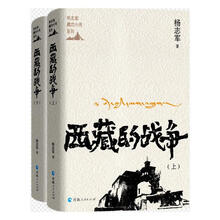回忆小时候读词,当然是从选本开始的。有那么一种印象,仿佛小儿得饼,一下子一支奶油大蛋糕放在面前了,只是大口地猛吃,那后果可以想见,不要好久,就腻了。我这里是指张惠言、周济一派的选本而言。后来接触到浙派的选本,从朱彝尊到谭献,那是另一路,也许像是一盘橄榄吧。总之,选家的手段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把同一事物,裁剪、装点得迥不相同。不用说,这怕都不是真实的原貌。《选释》是否就真能体现了整体的真实呢,当然不好这么说,不过它没有上面所说的两种特点,则是真的。原因可能是选者站得高些,钻得深些,也更为清醒的缘故。有时候,我觉得选者在拒绝一些几乎尽人皆知的作品的诱惑时,是表现了很大的勇气的。例如,在贺铸名下,就没有选“梅子黄时雨”一词。
《选释》不只是选,还做了大量笺注、通释、评论的工作。
小时读词,正如前面所说大口吃蛋糕那样的特点,只觉得满口甜香,却难得细辨滋味。因此,读《选释》的“释”,往往就别有会心。譬如梦窗的“惆怅双鸳不到”,过去似乎就不曾细想过这指的是美人的鞋子。玉田“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为什么特别举出鸥来呢?白石“燕雁无心”“强携酒、小桥宅”“二十四桥仍在”,这些都说得非常合理、非常有趣.也都和过去的词话等不同。平老几十年前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书,都是力作。照我的旧印象,读了也颇有吃蛋糕之感。这里就不同。更精致、简约,因之也更多余味。但这浓缩、精炼,是从很厚实的基础上作起的。平老过去曾经说过:“文心之细,细若牛毛;文事之危,危如累卵。”这两句话我至今记得。说词,也许可以比作到词人的心灵深处探险吧。这是很困难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更需要灵敏的感觉。因此,这也应是一种科学的工作。
选者在说小山“临江仙”时,于“两重心字罗衣”句下注,先说“未详”,是非常矜慎的态度。下面就详记对此所作的探索。指出太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为小山“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所本。这是不大有问题的。他接下去又说:“前人记诵广博,于创作时,每以联想的关系,错杂融会,成为新篇。此等例子正多,殆有不胜枚举者。”这一节话说得很好,说出了前人作诗、填词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如旧诗话、词话中所说,某甲偷了某乙,某丙又袭取某丁,都不免迹近无聊。只要不是通篇的抄袭,只要用得恰切、出色,都应该承认是一种高明的“再创造”,不必七嘴八舌的纠缠。
在三里河的那个大院里,住着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是国内、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自然也有负责的官员。那天早上在黄永玉家里,我说起要去拜访钱锺书,永玉立即接口说,“那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大儒”。这使我吃了一惊,也觉得很高兴。高兴的是锺书在朋友中赢得了如此的爱重;吃惊的是“儒”这个字眼,竟自从最最最卑微的地位一下子恢复了本来的身份。乍一听,是有些刺耳的,可是随即禁不住使我放声大笑了。
永玉画画、刻木刻、打猎、养猴子和猫头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还写散文、写诗,知道的就要少一些。其实他还有一项出众的成就是说“笑话”,那是只有相熟的朋友才有领略的机会的。“笑话”,这字眼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有许多“话”并不可笑,甚至截然相反,只不过采取的是“笑话”的形式。例如,他告诉过我他们许多人住在“牛棚”时,一天三次走到饭堂去吃饭。排了队,低着头,手里拿着吃饭的家伙,谢罪、感恩,最后还要唱一支歌,食物才能到手。他为我唱了那支歌,弯着腰,带着极度的虔诚,歌声幽咽凄凉,真是不忍入耳。歌的结未是一个感叹的“哎!”出奇的是曲终奏雅,竟自饱含着欢快的调子。不能不佩服“天才”作曲家的出色安排。因为“哎!”过后就可以得到短暂的弛缓去填肚皮,而每次必然前来欣赏这种精彩保留节目的一大群孩子,这时也必将给他们一场喝彩与哄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