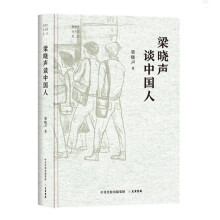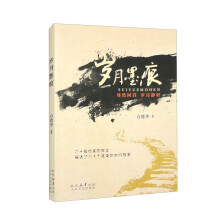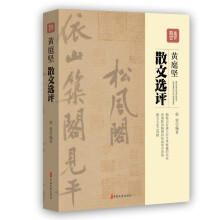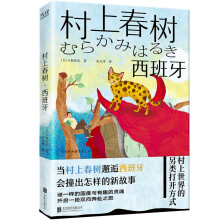开一束紫云英
记忆里的花花草草有一款一定是紫云英。紫云英纤弱、繁密、不起眼,花开时却一片锦绣,因为绵延成片,自成一种风景。吾乡人一律称其为红花草,及至长大我才晓得它的学名。
小时候和同伴喜欢将牛牵到紫云英丰美的地方,丢下缰绳去摘红花,一把一把地采来,与柳枝、老鼠花一起编结成花环。牛起先吃路旁的杂草,慢慢就伸长脖子去够紫云英,牛舌撩到哪里,哪里的花草就留下一片凹槽。这是不允许的,因队里要用它来沤肥料。花环玩腻后,我们就将它挂到牛角上,或者拴在牛尾巴上。戴着花环的牛昂着头望着远方,尾巴一甩一甩的,样子十分滑稽。红花草只留一点做种,大多不等到它结籽,就被犁耙翻到地下去了。
阳春德泽,万物生辉。抽薹后的油菜见风长,一畦畦高大茂密,很快遍野花香,蜂飞蝶舞。我读书的村小叫席井小学,建在离家一里多路的一个高岗上。坡上坡下一片金黄,还没有抽条长个子的小学生们,走在花丛中,只露出一个个晃动着的圆脑袋。乡下一年四季活跃着各种小动物,都是小孩们乐此不疲的玩物。我们捉小蝌蚪、花大姐,逮犟牯牛、蚂蚱、蛐蛐。男孩子胆大,挑鼻涕虫、逗屎壳郎滚粪球,甚至去捅马蜂窝。油菜花开时,蜜蜂大受伤害,被捉住装进玻璃瓶中,或被剪去翅膀糟蹋至死。有一天,为了捉弄一下新来的算术老师,几个促狭鬼男生故意弄翻了瓶子,蜜蜂满教室乱飞乱撞。底下躲的、追的、跳的、笑的,闹成一锅粥。意外的是,算术老师并没有因为蜜蜂事件责罚学生,这倒让几个捣蛋鬼觉得很没意思。
当陂田由金黄渐渐转为沉甸甸的青绿的时候,窄窄的田埂皆被遮住,做农活或者过路的人欲寻方便,非得找一处豁口才钻得进去。
油菜花开时,麦子亦开始分蘖、扬花、孕穗、结实。放学路上,肚子早唱空城计了,我们找出饱满的穗子,掰开,一粒粒丢进口中。灌浆的麦粒含有一丝淡淡的清甜,唇齿间时而还会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我们只觉得十分好玩。我们还吃过烧麦籽。麦芒泛黄了,穗子愈加茁壮,几人一合计,捡来树枝草秸,揪几把麦穗,架火炙烤,待穗壳微煳,趁热搓去麦皮,便是一粒粒青润如玉的烧麦籽,黏韧里带有一种特别的焦香味儿,直到兴尽而归。回到家,因为一个个小脸变得黑漆麻乌,差不多都会遭到父母亲的一顿训斥。其实烧麦籽并不宜多吃,吃多了“潮心”。
吾乡人习惯将蚕豆点种在麦地、油菜地的田埂两侧,一者不占耕地,再者春夏之交,清贫的餐桌多了一道应季的菜肴。蚕豆是头年秋天点下的,我母亲说“点蚕豆”,而不说“种蚕豆”,乡人大抵如此。铁锹扎下七八公分,锹把顺势往前一倾,三两粒种豆便从锹背滑进泥缝,脚尖再踢上一撮碎土,冬天施一次基肥,便任其生长。蚕豆实在是好东西,我至今犹爱,可以白蒸,炒雪里蕻或鸡蛋,做豆泥。彼时我祖母常做蚕豆米蛋汤,撒盐起锅后,筷子蘸一丁点猪油,蚕豆米和蛋花载沉载浮,清清亮亮。没有其他菜蔬时,我们姊妹就吃蚕豆米汤泡饭,蚕豆米碧青,嫩,入口即化,一碗饭扒拉扒拉就下肚了。
P3-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