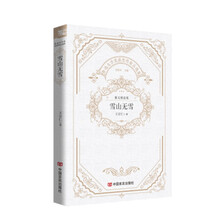油坊梁纪事
一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迁赶高潮中,银川各单位的一百来号人,被几辆卡车运到盐池县高沙窝公社,集中在公社礼堂,打地铺睡了一夜。第二天,我作为灵干户(单身一人),被一个生产队接人的社员看上,随他步行五十多里荒无人烟的沙路,穿过两道废弃的土长城,于日落时分,看到地平线上冒出树梢,再往前走是一个四面环沙、约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油坊梁。我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
到油坊梁的当天晚上,睡在生产队政治队长荀智家伙房灶台旁的地铺上。这是我油坊梁生涯的第一夜,时间是1966年9月25日。
第三天,按荀智的安排,由社员郭登明带我到一个大沙坝下面一间独立破烂土房子:这房子对扇门,门板经风吹雨淋翘--了起来,就是把门关上,门板和门框之间也可以放进一个拳头。土墙泛黑色,用手指一碰就掉渣。墙根鼠踪遍布,外面刮大风房皮沙土就往下掉。有个朝南的窗子,一块炕面那么大。房里有土炕,炕头有锅灶,炕和灶还有点湿,是新打的。郭登明说:“这就是你的家。”从我家翻过一个沙坝就是郭登明家,我从他家借来一小袋黄米,他从自家的柴垛抱来沙蒿柴,教我点炕--焖饭。他让我每天去他家提一桶水,他家的水是用毛驴从远处驮来的,也很金贵,分我一“桶”,此情难忘。
在这间破烂土房,我很快得到一批无私援助。
其一是郭登明老妈教我使碾推磨。村里不通电,我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用驴拉石碾把生产队借给我的糜子碾成黄米,用驴拉石磨把荞麦磨成荞麦面,才有做饭的基本食材。
其二是生产队一位大婶送我吃的东西。那是我到生产队不久,记得是中秋节,天刚黑,她突然来访。挎一个篮子,上面盖一块花布,揭去花布,下面是几个油饼、一小瓶油炸辣子,还有几个新鲜“酸圆”(山芋)。她对我说:“出门人‘汪晾’(可怜),你就‘罢’(别)想家了。”原来互不认识,我干恩万谢。她放下东西匆匆离去。后来,我知道这位老人是村南头王家大婶。她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对人说起这件事,而我只是在三十年后发表在《银川晚报》的文章里提到有人给我送吃的,又过六年在公开出版的《边外九年》里明确谈到王家大婶当年给我送油饼、油炸辣子、山芋。又过较长时间才打听到她叫乔生桂,搬迁到灵武县狼皮梁吊庄,人已不在,活到九十多岁。后来,我得到两张乔生桂生前的照片(孙立义女婿李跃全传给我的),珍藏在我的U盘里。
其三是小李子送来稻米。他是我原工作单位机关农场的农工,曾经借了我几十块钱,没有机会还我,心里不安。他带着二十多斤稻米,骑车一天半,摸到油坊梁。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感激之情,要留他吃饭。他说:“把东西送到了比什么都强,你慢慢用这点稻米。”他坚持立即离开。说实话,当年借了我钱的不是小李子一个人,但只有庄户人(小李子)没有忘记。我恢复工作后曾联系到他,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再后来听说他回了农村老家,命途多舛,也是命苦。
其四是杨家姑娘送我羊油坨。当年秋收结束后,生产队组织劳力去“外首”(当地群众习惯称内蒙古自治区为“外首”,生产队与“外首”只隔一条小路)拔苦豆子。往回走的时候,我落在最后。路过本生产队最北(bia,当地土音)头一户姓杨人家的院子边上,被这家一位小姑娘叫进家里,她利索地从伙房端出一碗白面条让我吃,我三口两口扒完。临走时,她又从蹲柜拿出一块羊油坨给我。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我拿了羊油坨就走。这块羊油坨解决了最初时日的吃油问题。她后来嫁到川区,详情不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