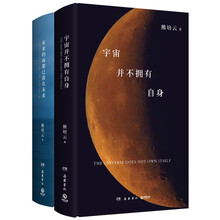湖
湖里已没有多少水了,那些来自云的水,来自梦的水,来自泽的水,都神秘地消失了,瘦成了一条线,一条像黄茅港老渔民的裤腰带一样,稍一用劲,就能掐断的线。
水退出的地方,成了滩。滩袒露着身子,展示着湖的秘密:有的地方深陷,有的地方隆起,有的地方平平展展。深陷的地方安静些,里面积着水,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潭。潭里有一些蚌在蠕动,也有一些上不得餐桌的鱼,无所顾忌地在游动。隆起的地方热闹些,潜伏了大半年的草,从泥里探出头来,热热闹闹地在生长。草里藏着一些鸟,一见人,就扑棱着翅膀飞起来,躲到另一处草里。平展的地方就更热闹了,杂乱的印痕证明,牛来过、人来过、车来过、鸟来过。车的印痕最明显,它可能打了一下滑,一个轮子陷进了污泥里,车烦躁起来,驱动着后轮,将大片大片的泥抛向天空。轮子下面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大坑,轮子后面一片狼藉。相伴着人的印痕的,是一些与湖无关的东西,几个矿泉水瓶、几个食品包装袋、几个烟盒在污泥里若隐若现,证明人有过不长不短的停留。这些印痕,将滩和岸连成了一体。湖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无休无止地挤压岸所获得的地盘,现在全都还给岸了。
堤似乎已被人遗忘了。人、牛、车、鸟的目的地都是湖或湖滩,堤成了一个站,一个人、牛、车、鸟偶尔停留的站。但只有堤才知道,此时看上去无比谦卑的湖,并没有屈服。不信的话,你可以沿着车辙走,沿着人的脚印走,走着走着,你就会迷失在湖里,走着走着,你就走到了沼泽里。沼泽,才是此时的湖真正让人恐惧的存在。沼泽在湖的中央,也可能在湖的边沿,它从不在乎湖水的盈缩,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它只做一件事,做湖的收藏者。它收藏水、收藏泥、收藏迷失在湖中的船和帆,也毫不犹豫地收藏敢于打扰它安宁的人。沼泽足够大,千百年的水文、千百年的风候、千百年的潮涨潮落都进了它的身体里,它躺在那里,湖就有了底气。
只有水涨起来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堤的存在。湖中每一次涨水都是从下雨开始的。开始是小雨,后来是大雨,后来是连绵不断的小雨、大雨。湖丰盈起来,丰盈起来的湖像一个盛装的少妇,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吸引着雨、吸引着从各个渠道汇集而来的水。丰盈起来的湖开始不甘寂寞,她伸展四肢,激起一层层的波浪。她招引风,吹着波浪一刻不停地向前挤,仿佛要把一湖的水都挤过堤,湖与堤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枯水期被堤、被人、被牛、被车夺去的尊严,湖都要分毫不差地夺回来。每隔三四年,黄茅港人总能在一个清晨起床时发现,湖越过了纤细的堤,伸展到了家门口,一大片正待收割的早稻成了湖的战利品。湖用一个晚上的努力,将黄茅港人半年的辛勤全收走了。
在黄茅港,所有的离别都和湖有关。湖战胜岸的那个清晨,田在水下,地在水下,房子也一半在水下的黄茅港人只能选择离别。他们选择一处岸,从岸上搭一块跳板,跳板的另一头搭到一只摇摇晃晃的船上。没有仪式,没有送别,一只船就这样载着无数个家庭的希望,开始四处漂泊。鼓荡的风如一根根的缆,牵引着这些茫然的船。漂泊者大多并没有远行,船到岳阳门,他们就下了。他们在岳阳的码头上留下来,他们的一双脚站在水里,肩上扛着一袋袋的货物,水在他们的脚下“吧嗒”“吧嗒”地喊,仿佛承载货物的不是肩、不是脚、不是人,而是水。漂泊者在水的喊叫声中,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承载一场洪水带来的损失。也有不幸的,借一次远行,他们选择了长久的离开,他们一直在漂泊,在寻找。水在流、岸在移、船在晃,离开时,还是青涩少年,归来时,已是满头银丝。最不幸的是村里的汉爹,中年丧妻的汉爹,一场洪水后,和村民一道踏上求生路,一趟远行,从此不知所终,抛下一大堆儿女在泥泞中顽强地生长。每年的清明,他的家人,总要在湖堤上插几朵纸花,倒一瓶酒,声嘶力竭地喊几声,让一个漂泊的灵魂记住回家的路。
湖水终于退了,她像丧夫的寡妇,哭着、喊着,跌跌撞撞,一步一回头地极不情愿地退回了湖里。昔日的浓妆艳抹、昔日的妖娆不群,最后都被秋风剥离,她被还原成一条一掐就断的水带,像被遗弃了一样,龟缩在湖心。
湖水退后,湖安静了,堤开始热闹起来。一场洪水,让大堤伤痕累累。漂泊的村民回来了,他们没有回到村庄,而是回到了堤上。他们睡在岸上的茅草棚里,吃在堤上。一只铁哨指挥着一个茅草棚。他们自带行李、自带工具,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用锄头挖土,用推车、用箢箕运土,将一车车的土运到被洪水掏空的堤上,去补一个个空荡荡的洞。这种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比漂泊更让人憋闷,有村民想过逃离,去继续他的漂泊梦,但没有人成功地脱离铁哨的束缚,他被拦住了。一大群人,用一根绳子缚住他,牵着他从堤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他走一步,哨声响一次。他像小学生一样,被绳子、被哨声牵着在堤上走过来走过去,一直走到完全忘记了为什么来、为什么去、为什么走,走到完全顺从哨声,他的一切就安定了,再没有人去烦他了。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