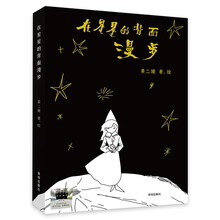引子
我的老家,有山之南,有水之北,早在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县枞阳。山是奇峰异石,青绿的山,山谷里还有座庙,水是澄澈碧绿有灵性的水。明洪武元年(1368年),一支毛氏族人从寿春迁居枞阳,来到麻山现在的杨家山脚下。毛氏族人发现此处遍布陶土,泥料质优,便以冶陶为生。制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了,世世代代沿袭着。
“小缸窑”便借以籍名,古有窑干、天街之称。
“小缸窑”,挺写实的名字,单看这名字你便能认识它的地域特色。一条老街婉转三五里,绵延着穿山绕梁,又隐没在一片无尽的原野、河汉、村庄、山峦里。如果说她们是一株参天大树,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发生在这里的事,便是她们的枝枝蔓蔓。
天峰禅心
少年的我,时常会和小伙伴去爬那条进山登顶的小路,山那边有桃花红、梨花白、杏儿黄的诱惑。山路一点点往上盘旋,逼仄而坚实,间或有几级石阶,两旁毛草灌木披覆,或许还能看见野兔、野獾子、豪猪的巢穴,那些小兔子可不怕人,支棱着耳朵蹦蹦跳跳,倏地就不见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走着这条进山的小路,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
进入山的腹地,坡道陡然,依着山势是垒起的石壁。石壁显然是人力堆砌的,黑褐色的点点石斑,老旧的苔藓深黑深绿,新长的苔藓透着翠绿,层层叠叠,粗壮的藤蔓纠缠不清……真是“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
两片茂盛挺拔的竹林深处,是一方开阔地带,那里常常是我们盘磨的地方。荒芜的乱草丛中,是横七竖八的石柱、石廊,古旧的青砖残瓦,缝隙里那些荒草荆棘伸出顽强的身腰,疯长着。父亲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座寺庙,寺庙两进,气势恢宏,有个和庙宇一样响亮的名字“天峰庵”。这些撒落的砖瓦、玉色细腻光润的铭碑似乎告诉我,这座庙宇往日的不同凡响。父亲还告诉我天峰庵源远流长,历史上劫难无数。而每一次劫难之后,总能奇迹般的再度辉煌。
据现在的天峰寺记载,早在宋时,清远禅师于麻山建成龙门禅院,彼时的杨家山满山遍野的山麻,麻山的名字便应运而生。麻山又因镇锁舒桐怀潜四邑之水,古称龙门。南唐散骑长侍、大学士、文学家徐铉贬谪连城,曾作《龙门寺记》。乾隆年间张廷玉次子、进士张若澄题写天峰寺门阙。
清朝的遗老遗少、文人学士常聚于此,乐山乐水,论诗谈禅,流连忘返,留下了许多锦绣文章。清末桐城派首要人物,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教育家吴汝纶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举为“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吴汝纶与天峰庵曾有过的缘分,却是鲜为人知的。
《吴汝纶全集》对天峰庵就有一段写实的文字,打开它就如打开一段尘封的岁月,那遥远的天峰庵不再扑朔迷离。父亲的故事也找到了有力的依据。
明末,吴氏族人君友舍宅为寺,清幽的山谷便有了晨钟暮鼓、梵音袅袅。杨家山还是张相国的祖坟地,山前是一条清丽的浣河,那片山挡束了邪浊之气,相国家人以为有利风水,便买下了那片山,也越发看重天峰庵,且有“绰楔”树立。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庵堂慢慢毁了。
咸丰年间,杨家山来了一个比丘尼,老尼见山色清奇、河湖浩瀚、波光敛艳,便决定不再走了。云游四海多年,老尼终于看见了一方清静宝地,便倾其所募银钱,重新修葺一座新的天峰庵。自此“橐橐”的木鱼声又敲醒晨曦,辞别暮色,香火日盛。
忽一日,来了一个游方和尚。和尚是个不折不扣的“花和尚”,说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吃喝嫖赌样样沾。老尼恐他污了佛门清静,几次三番坚守山门。和尚恶念顿起,天峰庵在一把邪恶的大火里化为灰烬。这些过往,县志和吴氏族人都有文字记录。
19世纪初,吴先生自里中,过天峰庵,取道安庆、南京,赴天津人李鸿章幕府。天峰庵此时的住持泰山正是老尼的外孙。吴先生登山小住,在庵里流连日许。《吴汝纶全集》里这样写道:“泰山年七十余也,而貌清腴,肌理润泽,与余辈年三四十人相若”;“今为屋二重;栋宇殊壮,诸佛像皆雄伟,皆泰山所募建者。其徒服习其教,事佛甚谨,猪、鱼、鸭、鸡,屏不入厨,有不食盐者”。泰山住持敬慕先生高才,曾经几次邀约,两人相见恨晚,秉烛夜谈。这样的风景名胜可怡情冶性,自然更适合读书了。
1923年,住持殷和尚将两进寺庙改建三进,供奉大小佛像十余尊。
时间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群扛着“青红棒”的人,在“破四旧”的呐喊里,将天峰庵夷为平地,便成了现在的样子,也给了我儿时竟至于圮废的记忆。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