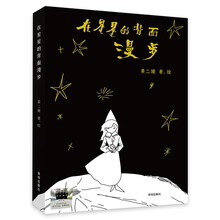乡土缘
此时,我正走在南塬黄土高坡的一条便道上,它从坡顶蜿蜒曲折地伸向坡底。这是春季雨后一个晴朗的中午,闲来无事,我同友人一同去城外旷野寻找渐失的乡间记忆。
脚下是熟悉的地形、庄稼和野草,弥漫在空中的是熟悉的味道。这片油菜地正盛开着黄灿灿的花,走近花丛,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忙个不停。地头空地里,长满了各种野草,有正开着小花的,也有熟识的猪草。儿时常去地里给家里的小猪寻猪草,那种从杂草中找到猪草的惊喜之情,又乍现于脑际。每每置身于田间地头,我便会想起过往的岁月,想起许多故人和趣事,一种少有的激动和亲切感从心头掠过。
这条便道把一级级小块的梯田连接起来,走到下一级,是一片近年新植的果园。一行行刚开过花的樱桃树,个头并不高,仅长出了三五个枝丫,仔细找寻,隐约瞧见豆粒大小的果实已经探出了头。这是一面向阳的高坡,难得被雨水滋润的土地虽旱了些,但春日舒适的温度,却让小果树们似孩子般愉悦地生长着。
脚下的便道,不知走过了多少人,才显得如此光亮、清晰,所幸尚未被新生的杂草遮盖住。我知道,这小小的便道是庄稼人收种庄稼时一次次踩踏出来的,像我这样悠闲的城里人是很少踏入这里的。整日和泥土打交道的庄稼人从小就熟悉这样的道路,这里不知沉积了多少代先祖的脚印。这无需刻意修整的田间小路,晴天扬浮尘,雨天很泥泞,甚或无法行走。只有等太阳把路面晒干了,庄稼人方能下地干活。
有时候,人们也会不避泥泞去地里劳作。记得小时候,年少的我趁着夏日骤雨初歇的间隙,便穿着娘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土布鞋,跟着爹踩在那泥泞的田间小路上,去给自家苞谷地施肥。不一会儿,泥水就打湿了衣服,脚上的鞋沾满了沉重的泥巴,我们一走一歪,艰难地穿行在苞谷地里。庄稼人这种惯常的劳作与生活,已经恒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五六米高的土崖上,长了酸枣刺、狗头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野生灌木。灌木丛里,紧贴地面生长着杂草,若是雨后,还会长出许多地软来。秋雨时节,我曾在那杂草丛里捡拾过地软。深褐色的地软,自然生长在潮湿的杂草根部,紧贴着地皮生长。我把地软捡回家,娘将其包在包子里,吃起来比肉还香。
满地的野草吸引我蹲下身子,让我又找回了那遗落于出村路上的旧情结。小小的野草,总是结伴而生,它们并不孤单,在小孩子的眼里,这是个无比美丽的世界。自然生长的野草,有的刚刚抽出新芽,有的正趾高气扬地向天而生,有的已经开花结籽。
车前子、枸杞、打碗花、秃苍花、狗尾巴草、香茅草、蒿草、马蔺草、扫帚菜、刺角菜……各种似曾相识的植物拥挤在一起,拼命地生长着。
我一眼便看到了一片蒲公英,在矮草丛里,那一根根细长的茎干亭亭玉立,轻轻吹口气,蒲公英的种子便四处飘散开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
夏日的路边,长着一种拖着长蔓的叫蒺藜的野草,所结的蒺藜核比黄豆粒儿稍大点儿,却满身带刺,人若不注意踩着了,扎得脚生疼。好多年后,这深刻的儿时印记,仍时时提醒我走路时得绕开那些恼人的蒺藜。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