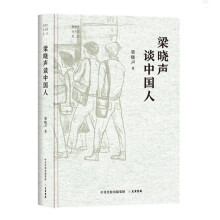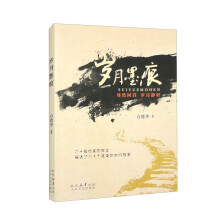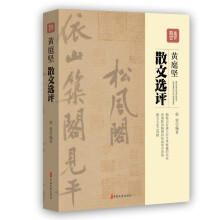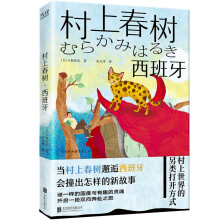《散步的路口/当代著名作家美文自选集》:
一天,两天,帐篷里的人只能用黑夜和白天来计算时间。废墟里捡来的衣服,菜园里拾来的瓜果,胡乱充饥和遮羞。余震不断袭来,黑色的污水从井里蹿起一米多高的水柱,残垣断壁轰然倒地,鸡狗惊叫着四处乱窜,大人孩子寻找着可作支撑的大树。灾难一次次笼罩着死里逃生的唐山人,没有人再相信父亲生还的希望。
太阳似乎也吓坏了,第三天才怯生生地露出头,窥探这片大灾过后的土地。尸体一车车运走,哭声一路连绵,灾难大片一样的镜头上演在每一个目光所及的地方。父亲单位来人了,说这次全省的会议,父亲下榻的招待所就是地震中心,让全家人节哀。我疯了一样把他们轰出帐篷,泣不成声地喊着:爸爸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固执地坐在路边,捡拾着路旁的石子。我相信,等我捡到一百颗时,父亲向我走来的画面就会实现。
从没见过那么美丽的晚霞,好像唐山人向死而生的倔强眼神,再次验证我们还活着,并把我的记忆定格在生命的最美瞬间。父亲回来了,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包裹着父亲的金色夕阳,似乎穿透了他的身体辐射开去。我扔掉手里的石子,一下子蹦起来,向着父亲跑着,喊着,帐篷里的所有人都出来了,一起跑着向父亲聚拢,然后把他围在中间,哭着、喊着、笑着、拥着……我站在人群外,看着大难不死的父亲和每一个人紧紧拥抱。他脸庞消瘦,眼泪滂沱,身上裸露的地方到处是伤痕,指尖上更是血迹斑斑。红色的绒裤与夏天那么不合时宜,左脚上一只黑色的袜子外套着一只黑色的凉鞋,右脚一只绿色的球鞋上脚后跟沾满了红黑色的血迹,上身是藏蓝色的防雨布胡乱地从肩膀斜裹在身上……我不知道生命的界限是不是从此可以划分,大难不死的人从此是不是可以长命百岁。此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还活着!最欣慰的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真好!
父亲所住的招待所一共五层,凌晨过后,刚刚还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上百个各行各业的精英,转眼只剩了五人孤零零地站在雨水里对望。望着渗血的钢筋水泥,三十五岁的父亲蹲在地上,放声痛哭。三十五公里的路父亲走了三天三夜,路上救了多少人,父亲没有数过;给多少体无遮拦的死者盖上块破碎的衣服,父亲更没有算过。他只说,三天三夜几乎没吃东西没喝水,实在走不动了,否则会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回来后,父亲经常对着他那辆自行车发呆,说如果不是它,地震不被砸死,也会淹死在那条河里。桥没有了,路裂开了很深的沟,只能涉水而过,平日里温顺的河流狂怒地咆哮着,水没过头顶的刹那,不会游泳的父亲彻底绝望了,没想到自行车稳稳地立在河心,父亲踩在自行车上越过了那条生死的界限。父亲说一定是那些一路上被他救助的人用意念救了他。
1976年7月28日,这个在日历上普普通通的日子,却深深硌疼了唐山人。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迷惑于人,而唐山人,从没想到以地震让唐山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他们生命里最需要剪切掉的就是这一段记忆,偏偏成了最难忘记的一篇。狰狞的岁月,在这块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重印迹。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刹那间,七千人家从此绝户,二十四万生命从此消失,到处是孤儿院、收容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