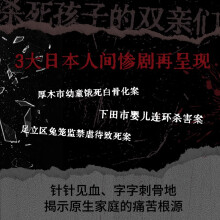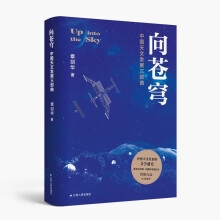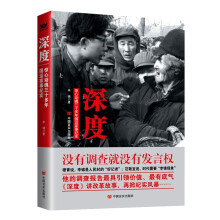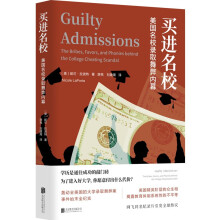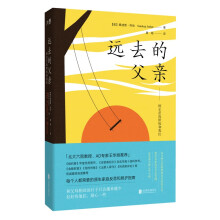1
有的话像块煤,刚听到时你没有在意,可是说不定哪天它又燃烧起来,温暖了你的心。
“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就是这种话。我不记得何时,在什么背景下,在下沙听过或见过这句话。起初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口号,或一条挂在墙上几天或几个月后就没了的标语,没有在意。
几年前,不知被记忆覆盖多少层的“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突然从心底冒出来时,我感到温暖,感到心头一热。不知这一口号是谁提出来的,我觉得他很懂下沙这片土地,也很懂下沙五万人民的期待与渴求。
下沙,位于钱塘江北岸,亦称“北沙”,它与南岸的沙地——“南沙”犹如骨肉同胞隔汀相望。它们本来血肉相连,至嘉庆十八年(1813),钱塘汀改道,下沙所在地区成为河道与岸北的滩涂。钱塘江南北两岸的广阔滩涂犹如一张宽达十几公里的巨型大床,任由潮水翻滚。它从南翻滚到北时,北岸就出现坍江,泥沙被潮水裹走,送至大海;它从北翻滚到南时,又把北岸的灾难复制到了南岸。
据史书记载,从唐武德六年(623)至新中国成立的1300多年间,有记录的钱塘江潮灾就有183次,平均7.25年一次;明清及民国时期,潮灾更频繁,平均4年一次。据《余杭县志》记载,1905~1948年间,七堡至盐官一带,江潮摆动范围仍有5—12公里,大坍江4次。钱塘江每次翻滚都会给岸边的百姓带来灾难,百姓或丧失土地,或家破人亡。 缪庭富出生在饱尝钱塘汀的恩泽与暴虐的农民家庭,坍江犹如一个幽灵盘踞在他内心深处。他第一次目睹坍江是在1949~6月,汀南的梅雨季,天空阴沉沉的。太阳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偶尔探出头来,没过一会儿就被赶跑了。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早起睁开眼睛时它就在下,晚上闭眼睛前它还没下完。空气犹如拧不干的洗澡巾,贴在身上,黏糊糊的。雨天,农民种不了地,盐民晒不了盐,只得蜗居在草舍里,等待天晴。
南岸的沙地,有农民仰望天空,满脸愁云地说:“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这还不算恐怖,恐怖的是梅雨季是钱塘江的潮汛期,风疾浪大,空中散发着黏稠的成腥味儿。一场接一场的雨浇得钱塘江暴跳如雷,汀水从上游火冒三丈地冲下来。
那天,缪庭富坐在学堂里的板凳上,听着身穿粗布衣衫的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着《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深奥、晦涩、卡卉燥和乏味,他哪里提得起精神?听着听着就两眼蒙咙,昏昏欲睡,脑袋像沉沉的稻穗耷拉下来。
“坍江啦,快到钱塘江捞东西啊!”
随着喊声,外边传来嘈杂声和脚步声,似乎有许多人在往江边跑。
这一下赶走了缪庭富的睡意,他顿时来了精神,脑袋像雄鸡似的昂起,脚伸到桌腿外,想蹿出去看看热闹。可是,当目光落在教书先生手里的戒尺上时,他的脚像啄谷粒的麻雀见到扑过来的大狗,惊飞似的缩了回来。缪庭富读了两年学堂,不仅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也体验过被先生打板子的滋味。先生四十来岁,看似儒雅,下手却很重,缪庭富被抽过几次。
“这次坍江不知冲走多少草舍?”外边传来忧虑的议论声。
缪庭富还没见过坍江,不过坍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生于萧山县新湾乡冯家楼,出生那天正好是农历六月十九,民间相传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村里的老人说,这孩子有菩萨庇佑,很有福气。对生活在钱塘江畔的人来说,这个月份的确很好。正值夏日,钱塘江恢复了母亲河的形象,一江碧水,波光粼粼,散发着慈祥的母爱。
新湾也叫新湾底,意思是新掘的湾到了底。新湾被盛陵湾分为两半。盛陵湾是沙地上的一条重要河流,它像一条蓝色绸带串联起了新湾的几个村落,如共裕村、共和村。新湾人喜欢临湾而居,盛陵湾的水可以灌溉农田,湾上水可以载舟,在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年代,这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舟楫之利使得新湾形成了较繁荣的集镇,虽不及西北部的大镇头蓬那么繁华热闹,但镇上也有不少小本经营的家庭店铺,有做蒸笼、箍桶的,有弹棉花的……
原来新湾的西北是小泗埠镇,直北是三岔埭镇。它们被坍汀一一吞掉后,新湾就靠近了钱塘江。冯家楼挨着汤家楼,那边有个横江湖,湖面宽约三四十米,可以通船。汤家楼往东五六里就是钱塘汀,新湾人称它为“直江”。潮汛一来,汤家楼便岌岌可危。
1947年秋天,冯家楼坍江。缪庭富虽没目睹到那惨烈的情景,却记住了那骇人听闻的“轰——趴,轰——趴”的坍江声。坍江的速度是很快的,眨眼的工夫,一片土地就没了。缪庭富的父亲缪瑞继是土生土长的沙地人,跟钱塘江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摸透了它的秉性,知道留下来凶多吉少,急忙划拉一下东西,领着家人仓皇逃离了冯家楼村。
P5-7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