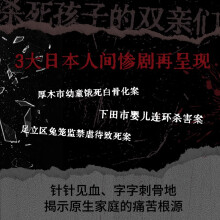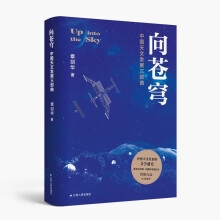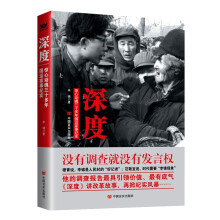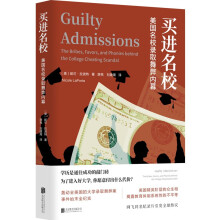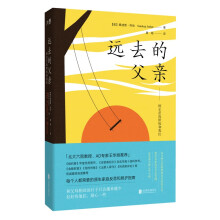2019年的一天,在从清远回广州的车上,我们几个朋友正天南地北地谈着文学、聊着生活。忽然,一位朋友说:“我是在大院里长大的,那就是我的故乡。整个城市就那一个大院是我的故乡,是我的根。后来,我们家离开了大院。对于我来说,到哪里都一样了。因为那是不可复制的。”他的话音刚落,车厢里都安静了下来。在底盘发出的咯吱声和时不时的颠簸中,坐在副驾驶位的我,扭过头去。他,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头扭向窗边,双手整了整笔挺的西装,又扶了扶他那金丝眼镜,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窗外。这个沉默的气氛持续了很久,直到另一位朋友提起别的话题,才把老教授的视线从窗外拉了回来。车里的人们又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但那时的我只是随声附和,而思绪已飘回了我的“故乡”。和朋友一样,我也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们的“故乡”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跟北京的大圈圈套中圈圈再套小圈圈不一样,我所住的院子压根就不在“广州城”里。那是一座老广州城根下的小院子。院子呈长方形,两条长边,一边靠着当时的广州市第27中学,另一边靠着盘福新街。
这个院子也是一座小城。刷着红油漆的铁栅栏将院子围得严严实实,仅在院子的西面有一个“缺口”,与院子的大门相互呼应。整座“城”的结构就是一个“曰”字。“字”外周的每一道笔画都是一幢苏式红砖楼。每幢楼都是6层高,整齐划一、方方正正,就像用尺子画出来的。沿着楼边走上一圈,隐隐然有种一位位英姿飒爽的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围绕着操场转圈踢正步的感觉。而“曰”字中间的一横,则是由一幢同样是6层高的苏式红砖楼和一个凉亭组成;被一横隔开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榕树和绿地。
小时候的我,最喜欢在凉亭附近玩耍。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不但是整个院子中唯一能落脚休息的地方,更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瞭望台。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可以见机行事,脚底抹油。我的家就位于院子正东面的红砖楼的2楼04房。对于一个全院出了名的“多动症”而言,找对路线溜得快,就意味着能少挨打。但其实可选择的并不多。东、西、北、中四幢楼的结构几乎完全一样,在每栋楼的中间只有一个上下的楼梯,无处可藏。在南楼倒是有一个旋转楼梯和黑乎乎的杂物间,藏个人还勉强可以。对我而言,经常不是满院子的追逐,就是在南楼里捉迷藏。
不管逃跑的结果如何,最终我都只能踏上那昏暗的楼梯,灰溜溜地回家。楼梯位于整栋楼正中的位置。在它的两边,所有的房间一字形摆开。紧挨着楼梯的是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我家的在左边,但我总是跑到右边第一间的门口。那里黑洞洞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只留下一条仅能一人走过的通道。尽头的灯泡发出微黄的光,那光连坐在灯下的老奶奶的脸都没法儿全部照亮。她每天都坐在那里,先用手将粽叶捋齐,折出尖角,然后就一勺一勺地依次填充糯米、绿豆,铺上一层五花肉,再用糯米填满,之后就将粽叶包紧,一边用牙紧紧压住粽绳的头,一边飞快地将粽子五花大绑。完成一个后,老奶奶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没有问题后,才转身放到身后已经码成小山的粽堆上。印象之中,这和观看楼下老大爷编扫把一样,是这座小“城”里唯二能够让我这个小毛孩旁观的事。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牛奶卡和钱,到大院值班室拿牛奶,然后就在大院门口旁边的老奶奶那买粽子。
我们这群疯孩子天天就在院子里东躲西藏,你追我赶。
P2-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