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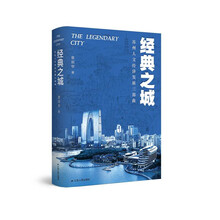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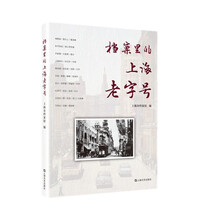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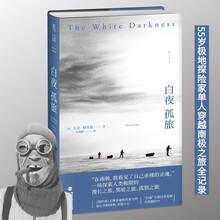
孤独的海
……
我在微信上给范梦海留言,问他,是不是经常觉得孤单?他回,是吧。觉得身边没有几个朋友能懂他。我说,人在高处总是这样的。他说跟我说话很舒服。我又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说,不考虑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他说,从来没想过结婚。
“是不是钱多了,眼光高了?”
“跟钱没关系。这只是个人的选择,国外很多有钱人选择单身。”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在微信里给我唱了这首《梦中的额吉》,他的声色不错,听上去有点像滕格尔。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首歌?他说,每次听就好像来到了蓝天白云下,特别安宁。现在这个社会太喧哗,人心太浮躁了,听点让人安宁的歌,挺好。
那次谈话快结束时,我提出想去他开的推拿店看看。之前,他跟我提起过,我所在的小城也有他合作的一家分店。可他说,实在抱歉,不能告诉我店名。很多人找他合作都是资金链出了问题,为了保护合作方的声誉,他不能对任何人说合作店的名字。合同上也有这一条,他必须遵守。
我心里纳闷,干这一行怎么有那么多规矩,跟地下党似的。但转念又想,合同上签订的事,别人不知道,他能遵守,说明这人靠谱。可能换了一般人,有这么大产业,早就在媒体上大肆报道了,要是这样,百度上关于他的新闻早就满天飞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连他的店都找不到。
过了一阵子,我又去了盲校采访。无意中认识了范梦海之前提到过的那位好兄弟,蒋海滨。
2003年出生的蒋海滨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海滨有一对名义上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名义上的弟弟。爸爸妈妈今年都六十多岁了,他们是在孤儿院工作的一对老年夫妻。海滨说,本来他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可因为他和他弟弟就打算再待几年,一直到他们俩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不再靠孤儿院的福利生活。
“有想过亲生爸爸妈妈吗?”
“很小的时候会想他们长什么样的,为什么会不要我?但后来就很少想了,因为想了也没用。”
“除了孤儿院的爸爸妈妈,还有学校的老师,你还有其他朋友吗?”
他起初摇头,后来又说,有一个哥哥,也是盲校毕业的,比他大十多岁。我问他,这人是谁?他说,范梦海。
我的心扑腾了一下,怎么那么巧?前几天,我还在采访范梦海呢。我问海滨,怎么认识范梦海的?海滨说,他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认识范梦海的。那一年,范梦海到学校参加一个活动,还到他们班来看望他的老师。
“班里那么多同学,他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可能觉得我是个孤儿,比较同情我吧。反正那天,他跟我说,想跟我做个朋友,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叫他哥哥。”
“你那时候知道他推拿店的老板吗?”
“知道,他那天还给我们班同学带来了很多好吃的,老师也有,老师还让我们跟哥哥学习,说将来长大了自己也开公司,做大老板。”
海滨说,那天他觉得很开心,结交了一个有钱的大老板哥哥。
后来,范就经常跟海滨电话联系,嘘寒问暖。那时候,海滨对哥哥很崇拜,觉得哥哥好有本事,长大了他也要做像哥哥那样的人。有时候,哥哥也给海滨寄好吃的。一次,海滨说枕头旧了,想换个新的。范梦海二话不说就给他寄来了一个新枕头。
“他对我很好,说以后,我大学毕业了,可以帮我找工作,还可以帮我找房子。”
“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海滨说,没有。但是,他能感觉出来,哥哥是个好人。六年级的时候,哥哥来学校找过他,要他好好学习。还说,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
“同学们是不是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位大老板哥哥?”
“应该有吧。不过,我们老师不让哥哥上台演讲。我们学校有很多学哥学姐,会把自己的一些成功经验带到学校跟我们分享,哥哥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哥哥说,没有必要四处宣传。”
“你很尊敬他是不是?”
“有点吧。”
海滨欲言又止。那天,老师找他还有事,我只能匆匆结束了跟他的谈话,想着下次再找海滨聊。说实话,范梦海在我心里不光是一个有为的企业老板,还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有志青年。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坐校车回家,我忍不住跟车上的老师谈起了范梦海和蒋海滨的事,我才说了一半,旁边一个短头发的女老师就打断了我的话。
“叶老师,他们俩的话你也相信?”
“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相信?”
短头发的女老师说,她是海滨小学时的语文老师。海滨第一次写作文,介绍他的家人,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他们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他和弟弟。爸爸妈妈都很爱他。周末他们会带他和弟弟去游乐园。节假日,他们会去海边玩。虽然,他的眼睛不好,可他觉得自己很幸福。
当时,她不了解情况以为海滨真有一个幸福的家,后来才知道海滨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从小就被爸爸妈妈抛弃了。
“那范梦海又怎么了?”我问。
这时,坐在我身后的海滨班主任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范梦海偶尔会去学校找海滨。平常多数是在手机上联系的。但据她所知,范这个人不太靠谱。有一次,范说,他有个在房地产公司的好朋友,等海滨长大了,他会想办法送他一套房子。当时,她也在场,随口问了一句,什么房地产公司,她也想买房子,能否介绍一下?范就支支吾吾起来,说,朋友也是刚开的公司,估计要过段时间才能稳定。
我把范跟我说的一些情况对海滨的班主任说了。她说,这些事她没听说过,让我最好打听清楚了。当时已经一月初了,再过一阵子学校要放假,大家都要过年了,因为家里杂事多,范梦海的事就暂时搁下了。
当然,我迟迟不跟范梦海联系,也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跟他开口说。要是直接问,怕人家会很尴尬。如果去当地调查,也要等到过年后。年前,大家都有一摊事,去了,打扰人家不说,可能还会坏事。
那就等到春天吧。我总觉得春天万物复苏,任何事情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可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政府下令居民没特殊情况不得出门。我只好在微信上跟范的老师和他的校友打听范的事,他们对他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范不太可能有这么多的连锁店。一,他没有那么多钱,据他以前教过的老师说,范家里条件很一般,他还有个弟弟。二,如果真像范所说的,他有那么多家连锁店,周围人肯定知道,媒体也肯定会报道。不管怎么说,现在政府部门,残联都很关心残障人的就业问题,他们肯定会宣传他。
为了确定范的情况,我找到了当地残联的电话。电话打过去,工作人员接了。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并说想跟他们核实一下范梦海的具体情况。那边的人让我稍微等一下。不多时,电话打过来了,说,范梦海在当地小镇上是有一家推拿店,店面不大,只有他和他奶奶两个人。我问,没有爸爸妈妈吗?那边回,店里只有一个老人和他。最近疫情排查,残联这边让他报工作人员信息,范说他的机构很大,有几十号人,可好几天了,范那边工作人员的名单一直没报上来。
残联的人说,他们会尽快跟乡镇人员联系,具体情况等打听清楚了,会跟我说。第二天下午,我再次接到了当地残联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12家连锁店估计没这回事。房地产公司的事,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小会的空白。
春节过后,新冠病毒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各地学校受疫情影响纷纷延迟开学。在家闲着,就从海滨的班主任那里要到了海滨的电话。电话拨通后,我问海滨,最近上网课习惯吗?他说,还可以。
闲聊几句后,我问到了范梦海。
“这段时间跟哥哥有联系吗?”
“有。”
“你对他的情况清楚吗?”
“知道一些吧。不过,他从来不跟我说家里的事。”
“哥哥跟你说过他的房地产公司还有他开了很多推拿店的事吗?”
“有。”
“你相信吗?”
“有些信,有些不信。”
海滨说,哥哥有时候给他打电话,如果电话那边有人来找他,他就会在电话里大声说,这个单子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可他每次见到哥哥,他都穿得很普通,也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如果哥哥真是个大老板,起码应该有自己的小汽车,即便自己不会开,也可以让公司里的司机开。而且,他每次寄过来的东西,都是没牌子的。有时候,他跟哥哥开玩笑说,想吃有钱人吃的东西。哥哥就说,不过是贴了个牌子,东西都差不多的。再说了,节约是一种美德。反正,老板哥哥从来不会给他买贵的东西。如果他提出来要几百块的东西,一般都会遭到拒绝。
“你怀疑他骗你,为什么还跟他来往?”
“他对我很好,经常会打电话给我。过年过节,他还给我买吃的,送我玩具。”
“你不戳穿他吗?”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吧。哥哥说,身边没有人能理解他,就连学校的老师也不理解他。我敢肯定,他不会害人。”
我想了想,问海滨,知道一首叫《梦中的额吉》的歌吗?海滨说,知道,还会唱。我问,是不是哥哥教你的?他说,是。
“哥哥说,我们都是孤独的人。”
说到这里,海滨的声音低下去。我似乎感觉电话那头,他在擦眼睛。我们的谈话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海滨要去上网课。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长长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再跟范梦海联系。也许,他要的是一种在幻想世界里的满足,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擦燃火柴看到的幻境,而我在恰当的时间做了他的那根火柴。或许,他身边很多人都充当过他的火柴吧。海滨应该也是。不,也许他们是互为火柴。在人群中,他们嗅到了彼此。
想起《梦中的额吉》里那句反复出现的歌词:睁开眼只剩下一个人孤单。忽然明白范梦海为什么会听着听着泪流满面了。
“哥哥说,我们都是孤独的人。”打下这行字,窗外的菩提树正在结它的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