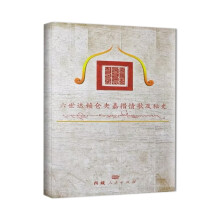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镇上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个,住在村子的最东头。这个村子,叫做芳村。芳村不大,也不过百十户人家。树却有很多,杨树,柳树,香椿树,刺槐,还有一种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叶子肥厚,长得极茂盛,树干上,常常有一种小虫子,长须,薄薄的翅子,伏在那里一动不动。待要悄悄把手伸过去的时候,小东西却忽然一张翅子,飞走了。
每个周末,父亲都回来。父亲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田间小路上疾驶。两旁,是庄稼地。田埂上,青草蔓延,野花星星点点,开得恣意。植物的气息在风中流荡,湿润润的,直扑人的脸。我立在村头,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近,内心里充满了欢喜。我知道,这是母亲的节日。 在芳村,父亲是一个特别的人。父亲有文化。他的气质,神情,谈吐,甚至,他的微笑和沉默,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把他同芳村的男人们区别开来,使得他的身上生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猜想,芳村的女人们,都暗暗地喜欢他。也因此,在芳村,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受人瞩目的人。女人们常常来我家串门,手里拿着活计,或者不拿。她们坐在院子里,说着话,东家长,西家短,不知道说到什么,就嘎嘎笑了。这是乡下女人特有的笑,爽朗,欢快,有那么一种微微的放肆在里面。为什么不呢,她们是妇人。历经了世事,她们什么都懂得。在芳村,妇人们,似乎有一种特权。她们可以说荤话,火辣辣的,直把男人们的脸都说红了。可以把某个男人捉住,褪了他的衣裤,出他的丑。经过了漫长的姑娘时代的屈抑和拘谨,如今,她们是要任性一回了。然而,我父亲是个例外。
微风吹过来,一片树叶掉在地上,闲闲的,起伏两下,也跑不到哪里去。我母亲坐在那里,一下一下地纳鞋底。线长长的,穿过鞋底子,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对面的四婶子就笑了。拙老婆,纫长线。四婶子是在笑母亲的拙。怎么说呢,同四婶子比起来,母亲是拙了一些。四婶子是芳村有名的巧人儿,在女红方面,尤其出类。还有一条,四婶子人生得标致。丹凤眼,微微有点吊眼梢,看人的时候,眼风一.飘,很媚了。尤其是,四婶子的身姿好,在街上走过,总有男人的眼睛追在后面,痴痴地看。在芳村,四婶子同母亲最亲厚。她常常来我们家,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说话,说着说着,两个脑袋就挤在一处,声音低下来,低下来,渐渐就听不见了。我蹲在树下,入迷地盯着蚂蚁阵,这些小东西,它们来来回回,忙忙碌碌。它们的世界里,都有些什么?我把一片树叶挡在一只蚂蚁面前,它们立刻乱了阵脚。这小小的树叶,我想,在它们眼里,一定无异于一座高山。那么,我的一口口水,在它们,简直就是一条汹涌的河流了吧。看着它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我格格地笑出了声。母亲诧异地朝这边看过来,妮妮,你在干什么——
在芳村,没有谁比我们家更关心星期了。在芳村,人们更关心初一和十五,二十四节气。星期,是一件遥远的事,陌生而洋气。我很记得,每个周末,不,应该是过了周三,家里的空气就不一样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也说不好。正仿佛发酵的面,醺醺然,甜里面,带着一丝微酸,一点一点地,慢慢膨胀起来,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还有隐隐的不安。母亲的脾气,是越发好了。她进进出出地忙碌,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提一些小小的要求,母亲多半会一口答应。假如是犯了错,这个时候,母亲也总是宽宏的。至多,她高高地举起巴掌,然后,在我的屁股上轻轻落下来,也就笑了。到了周五,傍晚,母亲派我们去村口,她自己,则忙着做饭。通常,是手擀面。上马饺子下马面,在这件事上,母亲近乎偏执了。我忘了说了,在厨房,母亲很有一手。她能把简单的饭食料理得有声有色。在母亲的一生中,厨艺,是她可以炫耀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资本之一。有时候,看着父亲一面吃着母亲的饭菜,一面赞不绝口,我就不免想,学校里的食堂,一定是很糟糕。一周一回的牙祭,父亲同我们一样,想必也是期待已久的了。母亲坐在一旁,欹着身子,随时准备为父亲添饭。灯光在屋子里流淌,温暖,明亮,油炸花生米的香味在空气里弥漫,有一种肥沃繁华的气息。欢腾,跳跃,然而也安宁,也妥帖。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样的夜晚,那样的灯光,饭桌前,一家人静静地吃饭,父亲和母亲,一递一句地说着话。也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院子里,风从树梢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墙根底下,唧唧地鸣叫。一屋子的安宁。这是我们家的盛世,我忘不了。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