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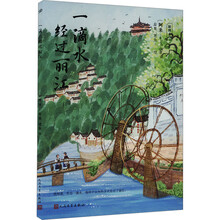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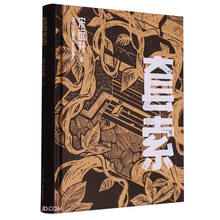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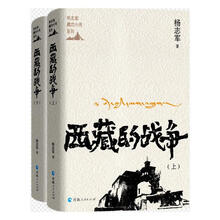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江年》之江与年,唯真与假,生与死,城与人的一次百年交锋而已。也许,读懂《江年》,世上再无爱情之祸。愿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都活在《江年》的爱情宇宙里。
很多年以后,他终于等来濒死一刻。
当最后一缕阳光开天辟地般进入眼帘的刹那,他神奇地想起了那个充满爱情和血腥的日子,这本在意料之中。
一切就像无情利刃划过崭新冰面。
那年,哈尔滨像在森林中走失的孩子,天上的光线时明时暗,脚下的土地泥泞不堪,每挪动一步都能感到危险,各种不怀好意的奇怪声响像怪兽的巨齿獠牙般错落起伏,顾不上迷惘、混沌和迟疑,只有恐惧、委屈和战栗。
他梦见他死了,他就真的死了。
这天的清晨,身着暗色过膝大衣的严世岱走进新城大街上的一栋公寓楼。稍微低头,小心跺跺脚抖落皮靴上的残雪。对着墙上的衣冠镜,缓缓端起双臂抖索一下大衣,面无表情地轻咳一声,声音显出几分老态,也有几分威严。他了解要去的楼上那套公寓的主人整洁干净,想到这一点,有些失落,鼻子一酸,薄薄的嘴唇哀伤地抽动了一下,尤其自责昨晚不祥的梦。
宽敞的房间布置简单克制,高高的棚顶上硕大的吊灯开着,发出暧昧的光,在阔气的实木地板上投射出奇怪的影子,让室内本就暗淡的自然光愈显清冷孤独。屋子里早有了一些人,小心翼翼,异常安静。
他在落落寡合的气氛里似乎看到了一阵清幽芬芳的幻影。严世岱的眼睛里出现了樱花,从屋顶的吊灯倾泻而下,穿越每个蹑手蹑脚的人视而不见的眼光,在地板上像雪一样融化,连个流连忘返的花瓣都没留下。在哈尔滨严寒的冬天,这种想象让严世岱有些奇怪,想起了日本人著名的谚语:“樱花树下埋死人。”他用瘦削高挺的鼻子刻意闻了闻,发现一种熟悉的味道在消失。他在上了年纪才知道,世上一切人都有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分有不同的味道,而这种始终如一的味道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或浓厚如酒或淡薄如烟,或陶醉近死或挫骨扬灰。
看到明显高人一头的严世岱进来,众人都默不作声,但眼神里对这位城中赫赫闻名的大人物流露出敬意,也对在这种场合遇到这位德高望重风度翩翩的长者稍显无措。一个警察恭敬地递过来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严世岱的名讳和电话,这显然是他清晨被电话惊醒的原因。严世岱缓缓接了过来,拆开信封,取出一张信笺,稍皱眉头,用一种尊重又不失身份的表情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小心放在衣兜里。
他谨慎地思索了一下,最后重重吸了口气,才沉沉移步到里间的卧室。这里落下的无数无辜的樱花被一阵邪恶的风裹挟着,正危险地扑向房间里那张曾承载爱情孕育生命见证誓言却在该死时刻羸弱不堪的床,深仇大恨死不罢休。
严世岱想到了爱情,危险的爱情。樱花和爱情在一起,这是严世岱从不对人启齿的想象。语言是身份的密码,修辞是心里最私密想象的涟漪,荒诞不经的比喻不好出现在一位严谨优雅的男人口中。不过,严世岱瞬间打消了路上的猜测,他罹患
了不能治愈的绝症,所以体面地告别人世,这其中别有隐情。
死去的是一位老人,这是房间内波澜不惊的原因之一。他的脸色暗青,如同稀疏的头发一般凋零、腐朽。只有眼睫毛还是黑色挺拔的,它和身体其他部分不同,只会告别,不会苍老。严世岱躬身端详了一下死者斑驳的面容,在褶皱不堪的皮肤上看不到任何扭曲的痛苦,而是一种逆来顺受、死而无憾,这让所有最后见到他身体的人感到欣慰。这个人此刻就像他的家一样,因为岁月沧桑而显得陈旧落寞,又因为喧嚣已尽显得了无牵挂。至于在他深深塌陷的皱纹之中还隐藏着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一根文明棍倚靠在床头,擦拭得一尘不染,在晨光的照射下闪现着规则、深沉、隐晦的木质纹理。严世岱暗想,求死之人因自私而高贵,身死之人因痛苦而丑陋。
他眯起双眼,抬起胳膊,伸出一只手指,微微勾着,似乎想责怪什么,但最终没说出话来。手指在半空中轻轻颤了几下,丧气地放下了。
周边的人看这位大人物没有嫌弃的意思,就搬过一把椅子。严世岱就势坐下,习惯性地跷起腿,又马上放下。他凑身轻轻握住死者的手,意味深长地慢慢摩挲着。严世岱手腕上的表闪耀着高傲的金光,光彩夺目地微微颤动,好像有一种能量在无声处积累、酝酿,会在山穷水尽的光景里如神降临,就像世上所有赤诚情谊的最终时刻。死者的皮肤虽然褶皱不堪,但有着和婴儿的皮肤一样的质感,轻柔、细腻却毫无伤害性。一定是因为爱的原因,才让历经岁月侵蚀的肌肤,在风停雨休之后又回复到初始的状态。这象征着所有的爱情,无论漫长炽热还是冰冻彻骨,都是初心使然。严世岱知道是这只手在昨夜的某个时刻写了这封信,字数不多,但浸染着庄严的情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几个动作,应该是悲怆和幸福的,毕竟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还可以掌控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没有一次死亡不是英雄的,能这样告别人世,似乎更像个英雄。
严世岱瞥见床头的写字桌上搁着一个深色小药瓶,用平静幽深的眼神抬头看了一下周围站着的警察,得到示意后才拿起来。这是一瓶安定药片,只剩下小半瓶,已被重新拧紧,放在一个空玻璃杯旁边。严世岱知道这是路新斋先生作为一位优秀医生的特点,无论什么时候都条理严谨。老路身上盖着一条陈旧但洁净的精美毛毯,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显然一直被精心保存着。严世岱欣赏这样的习惯,虽然老路医术高明收入不菲,但这种生活细节表明一个人纯洁的品性,他对所有其他事物也会如此讲究和认真。在他自由的天空中,克制是星辰般高贵和不凡的光。
在人们早已懒得提起的很久以前,年轻文雅的医生被严世岱姐姐的风采倾倒,在没有任何许诺的时候,就轻而易举被爱情一箭穿心。这个开场就自寻短见的爱情傀儡却从此和严世岱结下了深厚友谊,把命定的真诚爱屋及乌给了严世岱,而严世岱也投桃报李,视他为最好的兄长。这份情谊并没有因为路医生再一次投入爱情而稍显逊色,反而天长地久成全一段不逊于爱情成色的友谊。
严世岱年轻时从日本读书回来,就处于哈尔滨社交圈的顶层。作为城中富豪的唯一继承人,又喝过洋墨水,自然备受瞩目,他的声名鹊起就和这个城市漫长难熬的冬天一样自然而然。老路则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也有名气,他经常穿梭于城中官绅富贵的府邸之间。两个人在岁月的催促下不慌不忙地衰老,他们的友谊众所周知。
严世岱的身体格外好,七十多岁的人身姿挺拔走路如风,整日神采奕奕地出入城中各种社交场合,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这其中,少不了严家最信赖的医生无微不至的关爱。
英国毕业的内科专家无法根治灵魂的痛苦,像所有曾罹遭灾难的人一样,路医生眼神冷漠言语寥寥也多少能得到他人额外的体恤。也正因为这种内敛古板的做派让他更得城中名流的青睐,毕竟谁家的问诊信息都是隐私,交给寡言的名医才让人放心,路医生知道他获得的高昂诊费中包含着守口如瓶的费用,更让双方都心安理得。
最好的朋友都有一双相似的眼睛,其他的不同是曼妙的阳光打在人世间的不同角落,随缘认命就是。
两位老人经常要比一比书法。他们对流行千年的草书都不做评价,只是安心各自笔体,互相品头论足。
严世岱写的是楷书,端正秀丽,贵不可言。这是自小临摹颜真卿《多宝塔碑》的结果,落笔如刃落石,抬笔似鹤起舞,就像在历史的烟尘中寻觅到不老秘方,笃信云消雾散之后字字化金句句成玉。写不好瘦金体的人不是真正世家子弟,严世岱在书信中就会用瘦金体,一派舍我其谁的磊落王气,一纸情意婉约的谆谆美意,收信人会觉得气质超然深邃优雅可资信赖的严老板见字如面。
路医生的字体让人觉得特立独行,倒不是因为不认得,恰恰是每个字都认得,就像他的诊断,简洁清晰,不藏头不捉尾,准确得让人拍案叫绝。这是“爨体”,是隶书到楷书中间过渡的一种字体。隶书“蚕头雁尾”的少有飘逸已经变成了一种力透纸背的至拙,除了意义什么都不剩,反而凸显出造型艺术的强烈味道。至于楷书的精细和娇嫩,还是远远看不到的。这字看着简单,没有一笔三折声声慢,却能看到深刻的情感在山河日月中潜行不停。这种字在千年的时光中过渡成一种奇异的美,藏着书写者的秘密,永远无须抵达目的地,也就不必和盘托出,似乎是釜底抽薪的阴谋。
两人闲暇时,经常在中央大街的俄国酒吧里聚一聚。严世岱一杯咖啡之后就喝茶,让侍者端出最昂贵最精美的俄国茶炊,慢悠悠品上两杯。这时候,侍者就会贴心地送上来法国红酒,在客人面前熟练地开启。等到最后的程序会停顿一下,等严世岱凑近一些,再稍微用力,让瓶塞半湿半干顺畅无比的动人告别声准确无误传到客人耳朵里,从而被挑剔的主人验明正身纯洁无瑕。红酒醒上半小时,严世岱就会开始自斟自饮。路医生则不然,把糖皿和奶杯推到一边,一晚上从头到尾一杯接一杯苦咖啡。严世岱略有醉意,路医生也喝得额头冒汗。
有一次,严世岱对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产生了兴趣,和路医生请教个没完。路医生知道老友的心思,他不厌其烦细致地讲述了达·芬奇对于人体构造的精准分析,同时不露痕迹地巧妙告诉最好的朋友女人身体只有专业医生才了解的立竿见影的秘密。就这个话题,严世岱看似无心破天荒说起了爱情。路医生却突然喝干净一杯苦咖啡,拿起餐巾小心擦了擦嘴,也没看严世岱,云淡风轻到含糊不清:“总有人盼你死。”
人没到一定年纪,或者到了一定年纪,友谊就会显得纯粹。
两人常常在临近午夜才结束聚会。这节目繁多的每一个晚上,喝够了谈尽兴了,他们会在酒吧里扔一会儿飞镖,最终在
侍者的记分牌上争执谁为今晚买单。如果计分出现冲突争执不
下,一旁的台球室早为两个角斗士空出厮杀之所。
等路医生小心翼翼地拎起一旁的文明棍,严世岱则潇洒接过侍者递过来的阔边呢帽,再气宇轩昂地前后走出咖啡馆。严世岱让汽车在后面不远处跟着,他陪着路医生在中央大街走上一会儿,再从七道街的路口往东转,一直到新城大街路医生的住所,两人才礼貌话别,对酒吧里的争斗相逢一笑泯恩仇,结束一晚相聚。
此刻,严世岱怔怔地看着路医生的遗容,长长吁出口气,在冰凉的空气中划出一道长长的感叹号。他又抬头看看窗外,这是一个晦暗阴郁的早晨,萧瑟的景色本就让人郁闷不安,而此刻的警惕和克制更让人觉得压抑和伤感。严世岱站起身来,手背在身后轻轻搓动着,在房间内踱了几步,又站定仔细端详墙上的几幅相框。之前来做客注意过这几张照片,只是现在,才有机会靠近,认真地审视它们。人死了反而给周遭所有的人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
最正中是一张全家福,路医生和妻子还有两个差着几岁的小女孩,相纸有些发黄,就像他们曾经在这所房子里的时光,早到了该被遗忘的时候。
严世岱蓦地想起老路说起过,他和太太共同生活的时间是整整二十年。他的目光又落在并排挂着的一张照片,之前是隔着一段距离看,以为这是路医生年轻时候的照片,此时发现并不是。这是一张瘦削坚毅的脸,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眼神里是专业人士才有的倔强和自信,这样的人都是纯粹而孤独的,所以似乎和路医生有点相似。他盯着这张照片,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半晌,才想起来这是真正的大人物——伍连德医生。他在数十年前那场几乎灭绝哈尔滨的鼠疫大流行中,不顾个人安危,用相当进步的医疗理念拯救了这座城市。路医生曾说起过,用西方神学的认知来说,他永远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守护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城市和人民只要统治者,不要守护者。
十几年前“满洲国”建立时,伍连德医生远走海外。多年未见,严世岱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来。路医生把他的相片悬挂在家里最重要的位置,和自己的家人并列,一点不奇怪,这是今天内心冰凉的严世岱感觉到的唯一一点温存,但这突然出现的温存反而助燃了悲伤的火焰。严世岱稍微仰起头,看着天花板,让眼角的湿润在旁人注意之前消失。路医生从没有跟严世岱说起过自己的隐痛——和伍连德医生的恩情过往,但他早从旁人口中知道了那段往事。
伍连德医生对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人有天大的恩泽,说是再造之恩也不为过,其中就包括路医生。至于因为幸存而永世生活在患难和煎熬之中,那又不是医生的职责了,反而更让医者的声名凌然苦难之上。就像不幸的爱情,不能责怪赐予爱情的神明,明智的人只知道感恩,只能知道感恩。
严世岱想起自己多年前曾恶狠狠说过的话:憎恨爱情的人和诅咒生活的人,像绞刑架上的绳子一样愚蠢和污秽。他到现在也没觉得自己说错了,只是有些后悔,年轻的嘴有时候只配愚蠢的话。
小时候,严世岱的爷爷告诫他,如果有人说,他能看到魔鬼的影子,能听到魔鬼的脚步,那一定是个无恶不作的骗子。
暗无天日的灾难来临之初,无辜的城市没有意识到大祸临
头。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路新斋专长在内科,也对傅家甸突然爆发的群体性死亡无所适从。刚开始,他理所当然认为这是贫民区肮脏环境和落后医疗条件导致的类似于伤寒一类的疾病,直到出于医生的责任参加了在傅家甸的义诊,看到病人高烧不退全身浮肿甚至出现类似于天花一类的疱疹,才知道大事不妙。
路新斋想起早年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在大航海时代,登陆北美的欧洲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土著的刀枪陷阱,而是当地蛰伏的传染病毒。当地人对这种病毒早已经免疫,但对初来乍到的欧洲人来说则是致命武器,无药可治。反之,欧洲人带来的潜伏在身体里的病毒也让当地人无可抵挡地大量死亡。
对于哈尔滨这座新兴的城市,大量欧洲移民聚集于此,东清铁路便捷地把欧亚大陆连通,同时也有可能把某种致命的传染病毒带到这里。不但路新斋绞尽脑汁建议使用的各种疗法毫无疗效,即便是哈尔滨、奉天的医疗界对此也束手无策,大批民众离奇死亡,而且病毒呈现出极强的蔓延之势。在哈尔滨的各个城区,乃至就近的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病例。民众对于周边日渐增多的死亡从悲伤到恐慌,最后陷入了麻木的绝望之中。路新斋悲哀地断定,这座新生的城市面对灭顶之灾,所有的繁荣将毁于一旦,最终成为死寂的废墟,而他无能为力。
生死关头,伍连德医生衔钦命而来,无惧各路成见,勇敢地判定这种病毒就是曾让欧洲人近乎绝种的鼠疫,并且迅速搞清病毒的传播机制,随之顶着巨大压力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阻断传染源,疫情最终才得以遏制。
路新斋知道,在鼠疫肆虐欧洲大陆的时候,很多国家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多,伍连德的出现让哈尔滨逃过一劫,也是神州之幸。很多年以后,哈尔滨已经富庶繁荣,成为北方的耀眼城市,记性好的人就说这座城市新生之际就渡过大劫,是必有后福的。
苦难只有落实到自己身上才有真实的意义。路新斋在察觉这种病毒危害性的时候为时太晚,义诊的时候不幸染病。陷入昏迷之前他痛苦地发现已经传染给整日相处的家人们,这种自责和悲伤让他在进入长达十数天时而清醒时而昏厥的弥留状态时痛入骨髓,不是因为疫病本身,而是百身莫赎将死不能的后悔使然。也许因为伍连德医生高明的医术,也许因为那种不甘心不放心导致的泼天生命力,路新斋竟然在鬼门关止步,奇迹生还。
他柔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因为他无穷无尽的悔恨内疚而重新绽放生命之花,在病毒的冷酷折磨下先后枯萎。
路新斋听闻噩耗从病床上恸哭着跌落在地,双手扒紧红砖地面的缝隙,就像中枪垂死的人,向病房门口挣扎,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着。他要出去,到外面的寒天冻地去,为妻儿送上一程见上最后一面。一个瘦削的身影出现眼前,用疲惫不堪但不容置疑的南方口音告诉他:“先生,你不能去,所有死去的人都会被集中火化,除去必要的人任何人不能靠近!”尚存理性的路新斋知道此事的分量和理由,他不能像别人那样用无知和浅薄的情感助燃邪恶的病毒之火。他指缝流出了鲜血,颤抖不止像个荒郊野外孤苦无依的弃儿,再之后就是长长地抽泣,最后“哇”地大哭起来。他的私心是用这种无所顾忌、惊天动地的哭使得自己窒息,让自己的五脏六腑知道大限将至,不要再存一分生存之想,他们的主人是必死之心。后来,那人蹲身面前,在绝望中他恍惚看到口罩上方那双悲悯灵性的眼睛,那是
善与勇气交织着道义与责任所造就的圣灵般的眼睛。路新斋一
刹那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惭愧和苟且。他最终听到那句语气淡定但气势万钧的话:“你还是个医生!”
再见到伍连德医生是疫情退却的两年后,新落成的哈尔滨传染病院大楼里。他拘谨地站在伍连德面前,听到伍连德决定不录用他的理由:“你是精湛的内科医生,擅长在临床,不需要在这里做传染病研究,这是对才华的浪费,医者的天职是治病救人而不是知恩图报,这就是医者仁心。你若有回馈诚意,不如放之世间,所谓医者无疆,爱人如爱己。”伍连德说罢就低头研究病例,再不抬头。
路新斋悄悄退出去。在把医生办公室的门轻轻关上时,同时打开了另一番人生。在冷酷的岁月面前,命运有时会心生怜悯,网开一面,给生活一线生机。
当伍连德在“沈阳事变”之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有人看到,在深秋飘满落叶的火车站站台,一个人站在远远处望着被众人簇拥的伍连德一家登上火车。汽笛响起的时候,他双手垂握身前,面向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深深鞠躬,长久不动,就像一座和爱情永别的雕像。再抬起头,沧桑的老人已泪流满面。旁观这一切的人刹那间明白,年老的人流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绝望。
隔壁房间传来隐隐哭声,打断了严世岱的回忆。他顺着门缝看到是路医生的俄国用人,这个女佣每天八点钟准时到这里为路医生准备早餐并开始一天的工作,显然是她报了警,而警察过来看到遗书就拨通了自己的电话。想推门进去安慰她一下,但眼光被走廊边上的鱼缸吸引了,鱼缸已经被清理干净一
点水也没有,养的鱼不知去向,前几天来做客的时候还在的。
严世岱停住脚步,索性打消了和女佣寒暄的念头。他转身回到了卧室,双手毕恭毕敬打开衣橱,迎面一排排崭新衣装,其中多数是价格不菲的毛料西装,几乎能和严世岱的媲美。他伸出手,一件件打量着和路医生克制本性背道而驰的昂贵衣服。愈加猛烈的樱花没有遮蔽严世岱的眼睛,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不同寻常的端倪,随后,走到电话旁边,拿起了话筒 ……
他突然想起,今天晚上是小孙子的百日宴,三儿子夫妇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并给城中很多名流都发了邀请函。虽然是不太平的年月,但是对于自己这样的大家族来说,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战争形势不是自己决定的,枪子儿没有落到自己身上前,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还是如常的。况且对于早已妥善安排好大部分财产的自己来说,这并不会让人不安,反而很期待,未雨绸缪是严世岱一生的习惯。不过深藏心底的樱花和爱情的想象,终究把他也裹挟到充满危险诱惑的风里,化作一朵不能自已的樱花。
对于冬天哈尔滨恶劣的交通状况来说,要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很近,时间有些紧,而自己还要回家换身衣服才好出席晚宴。所以,他要尽快。
严世岱趁着没人注意,回到卧室,把手上的表摘下来,攥在手里看了看,用大拇指在表盘上擦了擦,恭敬地戴在路医生手上。这块表曾陪他度过很多经久难忘的时光,其中也包括无数个与路医生度过的愉快夜晚。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朝夕相处的东西更能配得上他和医生天人相隔的情谊。
严世岱后退了一步,轻轻咳了一声,双手垂在两侧,在被
樱花淹没以前,深深鞠躬,转身向门口走去。
一旁的警察递过一把伞,说:“严先生,外面下雪了。”严世岱略挺了一下本已笔直的身体,轻轻扬一下手,知道司机会张开伞在楼下等。他顿了一下,侧身拍拍警察的肩膀,轻轻叹了口气,表达了这种场合必需的但不会被轻易解读的遗憾。屋内的警察心情都比较放松,正值多事之秋,否则,城中名医留给一位富豪遗书后服药自尽,一定会吸引来很多小报记者编排出一通无聊逸事,可如今,这些人已经像感受到寒冷的苍蝇一样不知踪影了。警局也不会有什么压力,写个报告给上面,就算万事大吉。自己命运未定之际,别人的生死连一块面包都不如。
窗外大雪下得正起劲,行人很少,只有零星的关东军士兵在路上走过,无精打采如丧考妣。严世岱坐在车里,看到外面一派萧条萎靡,断定这就是末世气氛。严氏家族,在这座城市经营三代人,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俄国势力、“满洲国”轮番登场唱大戏,刀光中闪身,剑影下夺路,迎腥风决断,淋血雨砥砺,筚路蓝缕坚忍万分才化作旁人眼中的春风得意黄金甲。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一转眼又到了不得不抉择的关头。
他隐隐预感这次与以往不同,很可能真是一次彻底的改天换地。对于政治局势的敏感来源于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漫长磨砺,已深深浸透到血液里,并被准确无误地传承下来。他记得父亲说过,万物的狂欢和绚烂,归根到底都会用绝望和毁灭偿还。城市可以重生,国家可以重整,而人的时光却比玻璃杯还不堪一击,粉碎得不成样子还会继续伤人,怙恶不悛。
在汽车的颠簸里,他想到这是平生第三次面对遗言,每一次都记忆深刻,都随之而来某种割裂,某种新生。他确信,因为他的忠诚和恪守,每一次都完整地实现了遗嘱本身和其所表达的意义。手中这封遗嘱还不同,立言人并不是自己的家人,内容也并不复杂,只有熟悉的耐人寻味的字体:“世岱,愚兄有劳。”
遗嘱是世上最稀奇的文本,企图了断生前的纠葛,总会适得其反惊起身后的人望穿秋水。这是遗嘱的秘密,死到临头的人希望自己会被忘记,而不是遗忘。想到这儿,严世岱倒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他好奇这次的割裂或者新生 ……